网络主播唱歌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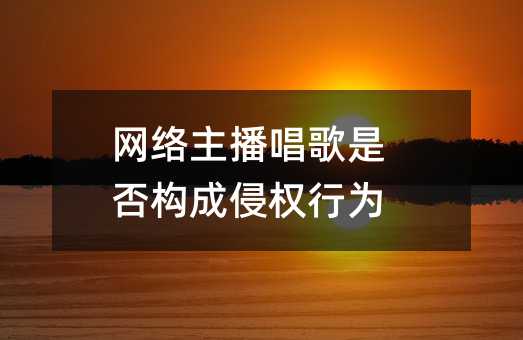
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进行唱歌表演,并通过各种名义的打赏收取费用,这被视为一种收费表演,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如果未经词曲著作权权利人许可进行表演,理论上主播可能构成侵权行为,而直播平台也存在共同侵权的风险。
一、取证难度大
主播的表演方式是直播,一般无法回看,因此权利人要取证只能去公证处,守着电脑开屏幕录像,并且需要两个公证员在场。由于直播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和周末,因此可能需要三个人加班取证。即使有回看功能,权利人取证的时间成本仍然非常高,因为必须观看整个直播过程才能找到具体的侵权作品。
此外,面对成百上千的主播,权利人很难确定维权对象。即使是四大唱片公司,每家都拥有几十万首词曲版权,要找到一位主播唱到拥有版权的歌曲也并非易事。
二、法院判赔标准低
假设权利人的律师和公证员经过几天的蹲守,终于录到一首主播唱的侵权歌曲,随后制作公证书并起诉至法院,前期成本可能达到几万元。那么法院会判决多少赔偿金呢?通常情况下,判决三千块一首歌已经是很高的赔偿标准。具体可参考与直播类似的公播权案例,例如全国首例超市背景音乐侵权案,判决总共1700元。
以往的案件中,版权人在维权音乐网站时往往一次播放或下载大量歌曲,通过批量维权诉讼来解决判赔标准低的问题。然而,直播这种模式与传统音乐网站不同,如前所述,找到一首侵权歌曲已经很困难,更何况如何进行批量维权呢?
三、著作权集体管理不力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新问题,而是唱片工业已经应对了上百年的问题。西方国家通过发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唱片公司共同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统一管理会员在某些领域的版权,例如营业场所的背景音乐和卡拉ok词曲版权。在维权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因为掌握众多权利,代表所有会员进行维权,效率非常高。
然而在中国,拥有版权最多的几个国际唱片公司很多并不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原因是根据法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经国际版权局批准,而国家版权局只批准官办的组织,并且它们收取的版权费分配方式存在争议。
因此,在直播领域,虽然需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维权,但这些组织却没有词曲版权最多的大公司的权利。
结论
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判赔标准对直播平台的商业模式而言存在版权红利。即使网络主播侵犯了作曲人和原唱者的权益,由于考虑到某些法律的空隙,很少有人愿意起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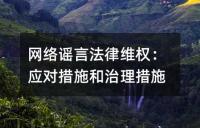
网络谣言的法律维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和治理措施。文章强调加强主流文化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完善公民网络行为法律制度,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创新,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等。同时,文章指出治理网络谣言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
-

网络商标侵权主体的确定问题,包括实际销售者、网络信息发布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搜索引擎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以及网络商标侵权的管辖问题。对于销售者和信息发布者的身份确定,北京市工商局采取登记措施。同时,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搜索引擎提供者虽不直接参与制假售假,但
-

网络著作权、网络商标权和网络不正当竞争等相关纠纷的审理指南内容。包括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举证责任分配、网页“快照”的合理使用、网络实时转播行为的法律规制等网络著作权问题;涉及平台服务商的行为属性与责任判断、“APP应用软件”与计算机软件商品或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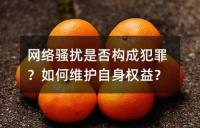
网络骚扰和网络暴力的问题。网络骚扰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如果性质恶劣,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被处以拘留或罚款。对于网络暴力,它混淆真实与虚假,侵犯个人权益,对当事人造成身心伤害,并直接影响其现实生活。同时,网络暴力对网民道德价值观也有影响
- 网络域名侵权表现类型
- 网络主播唱歌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 转载他人文章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