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出资能否成为股东身份认定依据

一、案例简述
2006年6月,被告XX市某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依法成立,2008年6月3日被告收取原告邓某某股金十万元并开具收据,但被告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亦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曾支付原告二万元分红款。2012年8月1日,被告委托律师向原告致函,告知原告十万元系被告以股金名义向原告暂借的,建议原告与被告妥善协商并办理退款手续,后双方协商未果。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确认原告为被告公司股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收取原告邓某某股金人民币十万元,虽然双方没有另行签订入股协议,但从十万元收款收据中被告原有全体股东的签名行为可以认定:被告吸收原告为新股东系双方合意行为。其后被告应当履行公司章程修改、记载股东名册、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书以及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等义务,被告未履行义务,不能作为不予确认原告股东身份的理由。据此,法院支持了原告诉求。
二、法律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的焦点问题在于,原告与被告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入股合意,原告出资的实体法律性质,被告能否以公示的方式形成的社会认知对抗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
1、合股合意问题。入股协议是以成立经营实体或以变更、扩大现有经营实体规模为目的,在出资人之间订立的确定彼此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结合本案,从十万元收款收据中被告公司原有全体股东的签名来看,此种行为的性质清楚、内容明确,是原告与被告原有的全体股东之间达成合股合意,并依此种合意履行出资义务,且被公司全体股东接受的行为。因此,该收条具有入股协议的法律属性。
2、原告出资的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但出资证明书只是一种权利证明,其功能在于表彰股东出资,本身不具有设权效力,因此,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备要件。本案中,原告出资的性质该如何认定?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1)被告开给原告的收款收据与被告成立时开给股东邓某某的收款收据相同;(2)被告委托律师向原告致函时,其已明确原告的十万元系“股金”;(3)2005年至2006年期间,被告已实际支付原告二万元分红款;(4)原告在收据上是以“主管”身份而非债权人身份签字的。据此可以认定,原告出资在性质上系股款。
3、被告能否以其外观记载对抗原告主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民商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涉及与外部相对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同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人合组织体,则主要涉及公司内部机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关系及组织管理关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相对人与公司交易,通常是通过公司的外观特征来了解和判断公司的资信状况,相对人不承担与公司外部表征不符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同理,公司也不能以其外部记载来对抗公司内部存在的股东身份争议。在本案中,我们尤应看到,在原告履行相关出资义务后,被告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未进行股东名册的记载等,系被告没有尽到对原告应有的义务,这些行为的不发生不能作为被告事后不予确认原告股东身份的理由,不能对抗作为善意出资人的原告邓某某,否则,既悖于公司法理,也违背诚信原则。
-

显名股东如何变更为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涉及《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等法条的解释和案例评析。文章指出,实际出资人想要变更股东身份、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等,必须得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不能直接适用反对解释,即使
-

股权转让协议的详细内容。协议涉及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包括背景、协议内容、股权的转让、甲方与乙方的声明、股东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以及争议解决等方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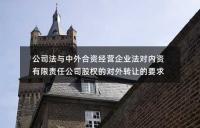
公司法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的要求
公司法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的要求。其中涉及内外资股东股权转让的同意权、外资股权转让的核准和工商变更登记、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及其条件限制、外国投资者出资未到位的股权质押及其转让的限制,以及外资股权部分转让后不得导致外资股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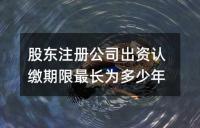
公司注册流程中关于股东出资认缴期限的问题。出资认缴期限由公司章程决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约定,无固定最长期限,且可后续变更。公司注册流程包括核准名称、提交材料、领取执照及刻章等事项,需耗时一段时间来完成整个注册流程。
- 股份制公司股东的法律责任
- 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股东以股权出资的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