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他人隐私视频是否构成犯罪行为?

美国的大法官这样表述隐私:“不被他人打扰的权利是所有自由的起点”。
今年10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准备推行网络实名制,遭到网民的反弹,笔者即是其中之一。现在,该协会犹抱琵琶,又声称尝试“有限实名”,即后台实名而前台任意。但,披了个马甲就认不出来了吗?就“实名”而言,前台的任意名就是后台的马甲,绕不过潜伏在前台之后的眼睛。就“实名制”言,有限云云,不过换汤,药还是那个药,当然也绕不过网民之眼。
这次出来发言的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理事长,这位人士说:当互联网用户要在网络上表达意见时必须在网络后台登记自己真实的身份。语出“必须”,可见权力。就网络实名或变相实名,我的意见没有变化:我发言什么和我如何发言(实名还是任意名),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它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受现行宪法保障的一项权利。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官方色彩,我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权力规定我必须实名说话或变相实名说话。我上次举的例子是,连民主投票都可以匿名,网络发言为什么不可以。
当然,权力自有它的理由,因为“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不是无限和绝对的”,后台实名可以“平衡个人隐私、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而“不是把个人隐私绝对化”。我们知道,隐私权是一种后起的权利,它是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即使就自由之乡古希腊而言,它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但却没有在公共事务之外的私人自由,当然也包括当时根本就无从意识的隐私自由。这种自由远到20世纪才逐步进入西方民主国家。转就权利和权利意识后发展的中国而言,隐私作为权利虽然正在逐步被意识,但,远远谈不上什么“个人隐私绝对化”,而且也没人要把隐私绝对化。难道仅仅网络不实名就是隐私绝对化吗?这话本身才绝对,而且还是权力绝对化的声音。
所谓隐私,乃是指一个人不被打扰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被知道就是被打扰。而不被知道,既针对权利之间的关系,也针对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就像我投票,既不想让我身边的人知道我投谁,更不想让权力知道我是否投了它。如果实行网络后台实名,那么,在我你他之间(即彼此的权利间),我的确有隐私,任意名的马甲使你和他不知道我是谁。但,在我和权力之间(网络后台正是它的辖地),我却是光着的。我的那些不想被你和他知道的信息,却被权力知道得一清二楚。隐私,如果只是对权利是隐私,对权力却不是,它还是真正的隐私吗?至此,我才读懂这位人士为什么反对个人隐私绝对化。原来,隐私只能相对于权利而言,在权力面前,隐私是绝对不能成为隐私的,否则就是绝对化。[page]
隐私属于个人,取消它,最方便的说法是抬出国家。后台实名的理由响当当,是为了平衡个人隐私与国家利益间的关系。事关国家,谁还说不。不!个人与国家,关系如此紧密,正如19世纪法国学者贡斯当所说:“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同理,由全体人民构成的那个国家也毫无价值。因此,权力的任何举措,包括这里的后台实名,都必须充分考虑公民个人的价值和权利,甚至意见。在现代社会,隐私对个人来讲,价值排序相当靠前。上个世纪,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道格拉斯曾经这样表述隐私:“不被他人打扰的权利是所有自由的起点”。是的,不过是一个网络发言,网络本身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地方,我却“必须”让后台那只“看不见的手”拿捏住我。不管权力是以什么名义,我都感到这是对我的不被打扰的权利的打扰。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后台实名是针对网络发言,网络发言和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莫非权力把发言视为损害国家利益?否则为什么要追究发言的实名,准备秋后算账?其实,公民个人在公共领域中发言,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怀。权力,不要以为只有你才代表公共,公共本来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公共,我们其实更关心,因为它直接关涉我们自己。
邵建
-

刑事判决书的在线查询、定义、概述、指导和制作注意事项。人们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在线查询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无法查询。刑事判决书是法院对刑事案件审理后依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书面决定,分为第一审和第二审。制作刑事判决书时
-

原告因被告公司在其网站上刊登涉及个人隐私的文章而引发的侵权纠纷。原告提交证据并请求法院依法裁判,主张被告停止侵害名誉权、隐私权,删除侵权文章,并赔偿精神损害和承担诉讼费。本案涉及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
-

名誉侵权案件中的证据要求及确定名誉侵权责任的要素。涉及侵权事实的证据包括文字、音像制品、口头及其他形式的侵权证据,侵权后果的证据需证明直接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法人需提交资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诉讼需授权委托书。确定名誉侵权责任考虑主观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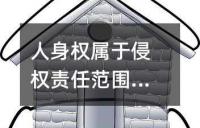
人身权是否属于侵权责任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包括人身权益的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文章详细阐述了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医疗期间产生的费用、因残疾产生的费用以及因受害人死亡产生的费用等。同时,提到了最新资
- 工资明细是否属于个人隐私
- 医疗机构泄露隐私的法律责任
- 网络侵权案公证书无效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