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刑事诉讼制度考:从历史角度审视宋代的刑事司法程序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概述
作为唐代以后封建法制发展最为辉煌的宋代,其法制的发展除了借鉴了唐律外还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个性的“自立一王之法”。本文试图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框架下建构一个完整的宋代刑事诉讼制度体系。
一、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热中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带来了各来矛盾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文明最前列”。宋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其法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自己个性的。虽然在我国法制史理论界,普遍的将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全盛时期,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宋代法律制度的考察 ,轻视了宋代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略的地位。事实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唐以后在法制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本文将详细考察宋代 法律制度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部分,并对一些制度与唐代进行了比较。
二、宋代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
《宋刑统》中有捕亡律一章,其条文内容相当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逮捕拘留的一些规定,在当时是作为政府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来使用的。 本文只论述其中的与逮捕犯人相关的内容。
三、宋代的刑事司法机构
两宋的司法机构包括各级审判机构、复核机构以及司法监察机构。宋的审判机构及其职权基本上是承袭了唐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审判体系,按不同审级确定了不同的审判权,根据犯罪对象又设有兼理审判机构和临时审判组织,使宋代的审判体系更加完整。
1)宋代的中央审判机构。宋代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太宗淳化二年(991)“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之后,大理寺的职权改变为“但掌天下奏狱”而“不复听讯”,也就是说大理寺成为只依法决断地方上奏案的慎刑机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7)“复置大理寺”,凡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流罪以下案专决,死罪案报御史台“就寺复审”。为避免大理寺在审判中出现失误,在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设三案、四司、八房,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元丰6年(1083)又将左断刑分为断、议两司,凡断公案皆送议司复议。右治狱设左右司、驱磨、检法、知杂四案,掌决京师刑狱,并“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元丰改制后,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权,但是奏裁重案和招狱,仍有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的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进行审理,由皇帝直接决断。
宋代的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但是在刑事监察职能外,御史台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也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这个可以以下史料中看出,“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鞠”。
2)京师审判机构。两宋的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的审判权由知府行使,,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审判的刑事案件都需要报大理寺审查,送刑部复核。但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罪至徒以上者,并须闻奏”,至此京师对杖以下罪有了判决权。
4)其它审判机构。宋代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定审判机构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审判机构,如某些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审判权,以及一些临时的审判组织。宋代对于军人犯罪的案件设有独立的审判机构,再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拥有监督审判军人案件的权力。中央设有殿前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号称“三衙”)各设推事,主掌“勘鞠、取会、追呼诸军班诸般词状公事”,设“法司,检引法条”。京师禁军狱案归三衙审理,“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若是大辟案件,则要“送纠察司录问,呈枢密院审核进奏”。南宋时的军人案件,由三衙和江上诸军都统制司的后司审理,这是专门受理本军案件的军事司法机构。在外戍守的禁军案件,杖以下的由本路提刑司“准法决罪”,“徒以下禁系奏裁”。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主要有“案议”、“制勘院”、“推勘院”三种,其中“案议”是宋代理断诏狱中的一种最高集议判决形式,主要在刑名有争和疑狱不能决时,朝廷召集宰相、谏官、御史、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级朝臣集议于朝堂(称为“杂议”),以议定刑名和集议判决,具有审判的性质。“制勘院”是当地方遇有重大案件时由皇帝亲差法官前往案件发生地临近州县置院推勘,“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 “推勘院”是对大辟或品官犯罪翻异案进行复核,由诸路监司差派清强官在案件发生地的临近州军置院勘推。
四、宋代的起诉制度
宋代没有专门的提起公诉的的机关,一般均由被害人或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起诉讼或由各级官府纠举犯罪。概括的讲同带的起诉方式主要由自诉、告发、举劾等几种。
1)自诉。自诉是指刑事受害人及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出的诉讼。宋代鼓励人们提起诉讼,通过设置中央鼓院、检院以及理检院来方便百姓提出控诉。
2)告发。告发是指受害人及其亲属之外的知情人对违法行为的检举。宋代的告发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自愿告发,主要针对的是一般性的犯罪。例如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下诏规定:“应典卖财产、影占徭役者,听人告。” 其二是奖励告发(也有称鼓励告发的),奖励告发一般针对的是某些特定的具体犯罪并且是在朝廷看来比较严重或在某段时间内需要重点打击的犯罪,对告发者的奖励包括物质的或官职,要经过固定的报批程序,由皇帝或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或由专门的立法规定。其三是强制告发,主要针对危害性大的犯罪,强迫伍保邻里、同僚、同居之人必须告发,若是谋反或盗贼等十恶重罪,不告发者将受到连坐的处罚。在宋代的某些时期甚至不知情的人也会受到连坐的处罚。
3)举劾。举劾是监察机关通过上下级和官司之间的互相监督、举报、弹劾而纠举违法犯罪的一种起诉形式。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和谏院,对地方的监察则有转运史和提刑司执行。此外州一级的通判也可以形式此项职能。对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机构将要受到处罚。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外,基层的耄保对百姓,各级行政长官对下级官吏,军官对士兵,以及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责任随时发现并纠举犯罪。
五、宋代的证据制度
宋基本上沿用唐代的证据制度,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
1)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在我国古代的诉讼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宋代的言词证据包括原、被告的供词与陈述和证人证言。关于言词证据的使用规定主要有①追摄证人必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定程序进行,且对于外地的证人追证要以最快的邮传方式,但是对于女证人“千里之外勿追摄”。 ②对于证人的放送的规定,仁宗康定二年(1040)规定:“自余连累若需要照证,暂勾分析,事了先放,只于案后声说。” ③对证人的关放日期专门作出了规定,规定2日放人且延长不得超过5日。④正犯重罪已明即不在追索轻罪的证人证言,对于命官案件罪状明白也不必追索干证。⑤对于没有证人或证据不足的可以申报上级或中央机关裁决,以避免司法官滥追无辜。
2)物证。宋代的刑事案件中物证据最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犯罪所遣返的客体,这些物证的收集是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的。在宋代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同时还规定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证物以验证口供的虚实,尤其是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值得注意的而宋代开始出现关于物证的理论,郑克在其所著的《折狱龟鉴》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件,系统的总结了治狱之道、破案之术和定案之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证据观念。
六、宋代的审判制度
关于宋代的审判制度中的审级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
2)宋代对结案条件的规定。宋代规定的结案的条件包括:①“本贯会问”即当犯罪者是外籍人时,再审寻结束而没有结案时必须派官吏到其原籍进行会问。会问内容主要为调查犯人“三代有无官荫”特权,是否具备“应留待丁”条件,是否是正在追捕的在逃犯,并将这些情况作为判决时宽贷或加重刑罚的依据。 ②重案在结案前必须经过检验,规定凡杀人或伤人等的重大案件必须委官进行检验,否则不得作为审结案件。③实行书写日历制度,即大辟罪犯及干连佐证人在领到的由上级官司统一印制的历纸上(一人一份)记下自己从入狱到审讯完毕每次提供的案情,同时也要求勘审官将每次提问的问题记下,并将这些资料作为上级官司检查结案成款是否合法的依据。④结案必须有供状。犯人供状原则上由自己书写,犯人不能书写的由典狱官代笔但需要向犯人宣读;审讯官也需要做审讯笔录并由犯人亲书画押,官吏做审讯笔录必须“据其所吐实辞”,违者“监司按治施行”;还规定重大案件要摘抄“录本”呈送上级审核,上级可以索取原状对照。
3)作出判决的程序规定。宋代作出判决的过程分为录问、检法、定判三个程序。录问是指在审讯结案后和检法议刑前,对徒罪以上大案差派没有参加过审判并依法不应回避的挂员对案犯提审录问,宋代对不同犯罪案件规定了不同的选差录问官标准以及确定了录问官的奖惩制度以保障其实施。在录问后,刑事案件由负责检断法律的法司根据犯罪情节将有关法律条问筛选出来供长官定罪量刑使用,宋代的录问还具有减少冤案的功能。在发司进行完检法程序后,依次为拟判(即由推官或签书判官厅公事等幕职官草拟初判意见 )—签押(即审判法司内的官员集体审核和签字画押)—定判(即由长官作出判决),在定判之前设置的程序杜绝了长官判决时随心所欲的情况,对于防止长官个人专断和减少刑狱滥用具有一定的效用。有学者将结绝作为判决作出的程序的最后一部分,对此本文不这样认为,而是将其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以及关于被告实施申诉权法律规定,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将有论述。
七、宋代的刑事复核复审制度
宋代的申诉复审制度。宋代规定犯人在审讯结案后的录问期间,宣读判决时的询问犯人是否服判时和行刑时的三个机会申诉,但是对申诉的形式作出了很多的机会,到南宋时期又规定只有取得了判决后才可以申诉,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对申诉的限制。宋代还对申诉的时效和程序作出了规定。宋代规定犯人的申诉必然的会引发复审的开始。宋代的犯人申诉制度中最为常见的是“翻异别勘制度”,即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若推翻供词或申诉有冤情,则这个案件必须更换审判观或更换司法机关重新审理。
宋代的刑事审判制度
一、翻异别勘制度
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审。然而,原审机关对于已经经过第二次翻异的案件没有权利进行移司别勘,而需要由上级机关的差官进行审判。为了防止囚犯滥用翻异别勘而拖延时间,宋代规定经过三次翻异推后的案件即使不复也要进行强行判决。然而,这个规定有两个例外:一是犯人高本推官受贿而冤枉他人,不受三推限制而继续进行别推;二是犯人称冤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受三推限制。
二、复审制度
有学者将宋代刑事审判中因管辖规定而产生的下级机关初审后再由上级机关审判的现象纳入复审制度中,但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下级机关事实上没有审判权,其初步结论对上级机关来说没有效力,上级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并不一定参考下级机关的初审结论。
三、死刑复核程序
北宋初期规定中央刑部在死刑执行后有权利根据各州的申禁状进行复查,然而这一制度存在弊端。因此到了北宋中期,州级机关对死刑案件的终审权被取消,由提刑司在执行前进行复核。当然,宋代对特殊时期的死刑可以免于复核,如因战乱而规定的强盗罪。总体而言,宋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滥用死刑的可能。
宋代的刑事执行制度
一、杖刑的执行制度
宋代对杖刑的尺寸进行了严格限制,长度为三尺五寸,大头不得超过二寸,厚度及小头直径不得超过九分。后来规定杖重不得超过十五两。杖刑的实施部位规定为臀部或背部。此外,宋代还规定了杖刑的行刑时间以及宽恤对象,如夜间不得行杖,老幼、疾孕等特殊情况可以减轻或免除杖刑,妇人犯罪可以赎罪等。这些制度体现了宋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二、徒刑的执行制度
宋代对徒刑的执行制度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首先,明确了收监制度,禁止犯人随带纸笔、酒、钱物和金刃等物品。其次,规定了犯人在监狱中使用的刑具的尺寸,如死刑犯戴枷,妇人和流罪以下犯罪者去掉狱具。再次,明确了系囚制度,根据罪犯的情况适用不同的禁制。此外,还规定了锁禁和枷禁等囚禁制度。另外,对于病囚给予医药救治,并允许其家人探视,并免去狱具。对囚犯的饮食、住宿条件、医疗和卫生状况等基本待遇也有详细规定。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严格执行,还规定了检视制度,对不依制度对待囚犯的要进行惩罚。尽管宋代的徒刑执行制度带有封建烙印,保护官吏和特权的痕迹,但对犯人生活待遇的规定以及对特殊情况的悯恤制度仍体现了一定的进步。
结束语
对于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研究,除了了解其发展与变化外,还可以借鉴古代的某些做法对今天的司法改革产生一定的参考作用。相对于对唐代法律制度的关注,宋代的法律制度及其价值在理论界上被轻视了。然而,对古代制度的考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和相关资料的支持。本文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详尽地概括了宋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并提出了对强制措施等方面的看法。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对于当时具体情况是否适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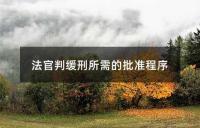
法官判缓刑所需的批准程序。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审理刑事案件后,会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评议,并分别作出有罪、无罪或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缓刑判决时,最终判决由合议庭做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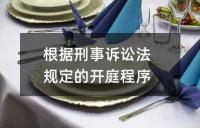
刑事诉讼法的开庭程序,包括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等环节。文章详细阐述了每个阶段的目的、内容和意义,强调了开庭程序在刑事审判中的重要性,以及保障被告人权益的必要性。
-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信用卡诈骗案的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彭某某因恶意透支信用卡被起诉,涉及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两张信用卡,欠款金额较大。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彭某某的父亲替其偿还了所有欠款和费用。法院根据证据和案情,对彭某某进行了判决。
-

开庭后判决书未下是否可办理取保候审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如可能判处较轻刑罚、不会对社会造成危险、患有严重疾病等,可以进行取保候审。同时,也明确了不得取保候审的情形。申请取保候审的程序和申请主体也有明
-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 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定罪数额及追诉标准
- 刑罚罚金的标准是多少钱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