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在法律上有强制性吗

一.讯问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强制性呢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警方在公开出版的教材《公安讯问》中,曾把讯问定义为“强制性问话”。 甫一面世,便遭来诸多非议,认为在当时的人权保护气氛之下,并不适宜存在强迫供述的观点以及做法。迄今为止,国内也很少有教材采用此种学说。尤其是近年来 法学界引入沉默权的争论后,许多法律研究者引入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及英美证据法中的“任意性自白”规则,主张口供的有效性、尤其是有罪供述的有效 性,应该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自由而自愿的基础上,回避、或者否定讯问的强制性,强制性对话更是令大家避之不及。
实际上,如果对讯问做一个细微的审视,我们不得不承认,讯问是一种法律性对话,而法律性对话究其本质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对证人作证的调查询问为 例,受到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调控,实体法上通过伪证罪等加以约束,程序法上,我国法律规定要告知证人其具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国外很多国家则要其当庭宣誓 等等。可见,即便是法律上的调查询问,也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讯问则实法律性对话中比较重要特殊的一种,它是就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与违法犯罪当事人的法律性对话。在我国法律中,公安执法主体的讯问有治安讯问,刑事司法主体的讯问有侦查讯问、检查讯问、法庭讯问等刑事讯问,和其他的法律性对话相比,它们都具有较强的法律强制性。
二.讯问前的准备有哪些
(一)全面熟悉、研究案件材料
检察人员先期的初查获取的案件材料,证据是讯 问的基础,因此,参加讯问的检察人员应全面熟悉和研究所获取的案件材料。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从其职务及社会经历等各方面分析其在讯问中的可 能的态度,为把握其思想动态打到下基础。另外,在审查核对案件的证据材料中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犯罪事实,了解侦查过程中获得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之间是否 有矛盾,还需要进一步收集哪些证据等,案件材料研究和熟悉的好坏,对以后的讯问的影响是深刻的。因此,在研究熟悉案件材料时要做好阅卷笔录,对案件的全部 材料和证据都要深入研究,并用多种方法加以验证。
(二)拟定讯问计划
检察人员在熟悉、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应确定讯问的具体内容、步 骤和方法,并将其形成书面材料。讯问人员应当将需要查明的问题,问题应该怎样提出,选择何事为突破口,采用何策略和方法以及如何运用等问题都要在讯问计划 中详细而有序的排列清楚,这样就会使整个讯问过程条理分明、层次清晰,否则容易使讯问工作缺乏系统性,讯问时丢三落四,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返工。另外,讯问计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讯问和调查所获得的情况不断的补充、调整,使讯问更具体。
(三)选择合适的讯问地点
讯问场所和周围环境对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刺激和影响作用都是相当大的。一般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都有固定的场所,如审讯室等,但应注意室内不要杂乱无章,要庄严、整洁、安 全,在查办渎职侵权案件时,对一些有权有势、有后台、有复杂关系网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在本地任何地方讯问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因此,对此类犯罪嫌疑 人最好实行异地羁押,这样才能打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优势和侥幸心理。
律师推荐:
北京律师 浙江律师 深圳律师 江苏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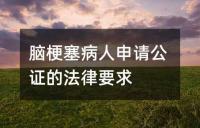
脑梗塞病人申请公证的法律要求。病人需提供头脑清醒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书,并由相关医院或鉴定机构开具。公证书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定,并需满足公证主体适格、出证程序合法、实体内容真实合法以及格式规范等条件。公证员进行公证时需遵循法定
-

伤害案件现场的处置程序和相关法律规定。警察到达现场后需封锁并勘验,收集相关痕迹、物证和生物样本。同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要求保护现场和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并立即报告。勘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需邀请见证人。人身检查和生物样本采集可用于确定
-

股东知情权的重要性以及实际操作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文章介绍了A公司作为B股份公司股东要求审计引发的争议,阐述了股东知情权的定义、目的以及公司法强制性和任意性规则对股份公司股东知情权的影响。文章指出,股东知情权既是约束也是自由度的一部分,旨在保护股东投资
-

共同抚养子女的方式以及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有利条件。夫妻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共同抚养子女,只要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离婚就会遵循双方意愿。在争取孩子抚养权方面,孩子的意见、收入状况、工作环境、居住条件、工作性质、性格修养、文化程度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状
- 只有购房合同能保全吗
- 公司未交社保签的劳动合同有效吗
-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的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