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医托是犯法的吗

目前在北京出现了众多医疗咨询公司。其公司员工绝大部分人假扮成医生,通过微信、营销QQ等新媒体软件和商务通软件,为相关民营医院“招揽患者”。这些“网络医托”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昆明等一二线城市,正不断向三线城市扩张。据悉,在一线城市,“网络医托”公司在一名患者身上平均能拿到1200元提成。医院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平均一名患者可以“开发”到6000元,乃至数十万元。
如果患者真有病,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卫生标准进行诊断治疗,那么“网络医托”最多不过是医疗过度市场化背景下生出的一个脓疮。尽管不受欢迎,但至少没有多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可问题是,现在的这些“网络医托”和关联医院已经结成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联盟”。“网络医托”基本没有专业医疗知识,唯一的兴趣就是把“附近的人”推荐给关联医疗机构;而相关的医院和医生则无视基本的道德操守,不管来就诊的人是否真的有病都会列出一长串的诊治措施。这个“联盟”恨不得将所有的人都“开发成患者”,进而从每个人身上赚足他们的医疗费。
毫无疑问,这种“网络医托”是十足的骗子,对他们应绳之以法。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但上述法律法规,未规定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故意将没有疾病的人诊断为有病并赚取诊疗费用”,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医托”就无法可治。我国刑法仍然具有打击该类行为的制度资源。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执业医师以赚取医疗费为目的,明知就诊的人没有疾病却故意提供诊治措施,或者进行“过度医疗”,那么相关行为可能会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网络医托”虽然没有参与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但如果明知相关医疗机构存在“虚假医疗”、“过度医疗”行为,那么其行为就与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形成了共犯结构,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犯罪。
目前已经出现了以诈骗罪追究“网络医托”和“黑心医院”从业人员刑事责任的案例。这些案件的查办对于遏制医疗市场的乱象,无疑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真正铲除“网络医托”和“黑心医院”生存的土壤,净化医疗环境,还需要建立起涵盖执业许可、行业自律、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的完整法律监管体系,建立能够公正、高效地查处患者投诉的执法机制。否则一阵风的执法过后,恐怕是又一次的“死灰复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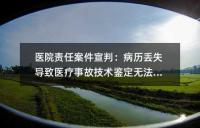
胡*斌因工伤导致的医疗事故案件。胡*斌在一家三甲医院接受手术后出现左肾萎缩问题,因医院丢失病历导致无法鉴定工伤致残等级。法院依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判定医院承担医疗事故责任,赔偿胡*斌共计80263元。胡*斌对伤残等级鉴定提出上诉,认为赔偿金额应更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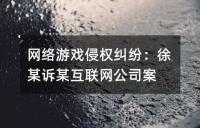
徐某诉某互联网公司网络游戏侵权纠纷案。徐某的游戏账号被该公司封停,导致无法登录游戏,引发侵权纠纷。法院认为互联网公司应证明徐某是否传播非法网站的行为及封停行为的合法性,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互联网公司撤回上诉。该案反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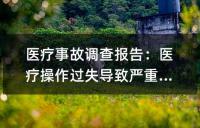
医疗事故调查报告,指出一起医疗操作过失导致的严重后果。医院未经家属同意进行阑尾切除术,手术操作不当导致并发症,需要二次手术修复。医院全责,构成三级丙等医疗事故,手术审批不当且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这起事件引发深刻教训,强调治疗应建立在确实存在疾病的基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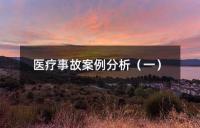
一起医疗事故案例。一名男性青年因恶性疟疾误诊为感冒而接受治疗,最终不幸去世。事故责任在于医生未按规定进行血检并及时确诊治疗。文章提出了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坚持各项诊疗常规等措施,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 医疗事故争议鉴定报告
- 医疗事故导致刘某伤残案件分析
- 婴儿一出生便“劫难”重重,病魔缠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