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合同对方不付运费留置其货物的条件

运输合同对方不付运费留置其货物要什么条件
案情介绍:运输合同对方不付运费留置其货物
2011年5月,原告某玻璃厂与被告某运输公司签订了一份运输合同。该合同约定由被告为原告运输玻璃瓶,被告负责清点货物数量、规格并签字认可,按原告指定的时间、地点将货物完好无损地交给收货方,并带回收货方的收条交原告入账,但未约定何时结算运费。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履行,原告陆续支付运费1.05万元,至2011年10月有1.29万元运费未结算。
2012年8月,原告让被告将价值5.3万余元的玻璃瓶运往某制药厂,被告却在途中将货扣至某仓库,并单方委托估价3.2万元。2013年3月10日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被告提出反诉,其以留置货物符合担保法为由,要求原告给付扣除各种费用后剩余的1.6万余元运费。
争议焦点:运输合同对方违约能否行使留置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能否行使留置权。
一种观点认为被告可以行使留置权,理由是:双方当事人虽未约定支付运费的时间,但根据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债权已届清偿期。被告行使留置权符合法律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不享有留置权。
律师说法:行使留置权的条件是什么
根据担保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得留置的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行使留置权与其承担的义务或者合同的特殊约定相抵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以上规定,以下情形不能行使留置权:
- 约定不得留置的物。
- 留置动产违背公序良俗。
- 行使留置权与合同承担的义务相抵触。
- 留置权行使与特殊约定的内容相抵触。
具体到本案,首先,合同未明确约定不能留置。其次,留置该批货物不违背公序良俗。然而,从双方约定情况看,本案被告应依约将货交给第三人,而留置权发生在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当债务得不到履行时,债权人拒绝返还留置物。如果允许被告行使留置权,必然影响第三人即收货方的权利,对收货方造成损失。这与其承担的合同义务即须安全、及时按指定时间、地点送到收货方是相违背的,因而不能行使留置权。这里指的合同承担的义务不是指返还物给债务人的义务,而是指其它义务,如涉及第三人的情况。最后,合同约定承运方不但运货,还应当对货物的清点负责,且交给承运人之后,须把收条交回原告入账,这是合同的特殊约定。被告的行为既与其承担的合同义务相抵触,又违反了合同的特殊约定,因此被告所谓的留置权不能成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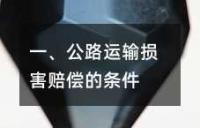
公路运输损害赔偿的条件及相关注意事项。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当事人违反合同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按《汽车货物运输规则》执行,包括限额赔偿和实际损失赔偿。保价运输中,保价金额与实际损失的差额不能作为违背公平原则的判断标准。合同中的公平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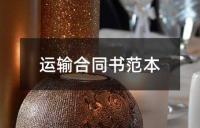
甲方与乙方之间长期合作的汽车运输合同的具体内容。合同书明确了货物的种类、性质以及合同期限。此外,文章还详述了货物发往地、运价及到货时间等相关事项,并对运输费用、到达时间等进行了具体约定。合同要求乙方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并保证运输过程中的责任不因其他
-

海事法院对海运合同的管辖权问题。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包括水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船舶相关纠纷案件等。海事诉讼管辖具有专门管辖、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等特别规定,原告可就被告原则进行起诉。在适用管辖权时,应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再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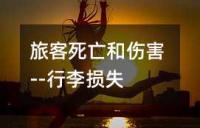
航空器事故导致的旅客死亡或身体伤害、行李损失、货物损失的责任问题。对于旅客死亡或身体伤害,只要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在操作过程中,承运人应承担责任;对于行李损失,只要事件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行李在承运人掌管之下,承运人也要承担责任。此外,还规定了运输合同权
- 运输合同的定义和支付方式
- 买卖合同履行地的确定
- 货物运输合同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