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收治精神病人惹祸端

精神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和限制
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精神治疗机构必须由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提出医学建议,才能对完全或部分丧失自知力的精神病患者进行住院治疗。尽管被告“精神中心”在本案中对原告进行了对话检查并认为其可能患有人格障碍,符合条例的形式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是合法的。
精神治疗机构的权力限制
首先,根据宪法和我国立法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和授权,并由专门机关实施。因此,精神治疗机构作为非司法和非行政部门,不具备对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患者实施强制收治的合法权力。《条例》规定的医学建议并不包含授权精神治疗机构采取强制措施的意义。
紧急救助的义务
其次,《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患者如果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或危害社会行为,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事发地公安部门应当将其送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然而,该条规定的救助义务和责任仅限于监护人、近亲属、单位和当地政府部门,其他公民和组织机构的义务是协助实施紧急救助,而不是法定义务。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发生暴力或危及他人的行为,因此不需要采取防范性的强制救助措施。
精神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
最后,精神治疗机构未能履行其作为专业机构应有的充分注意义务。根据法律规定,法定注意义务的高低应根据专业知识程度和是否职务行为等因素进行判断。作为上海市权威性专业治疗精神性疾病的机构,精神中心对疑似患者的精神疾病诊疗判断和收治保护等具有高于一般医疗机构或个人的注意义务。
然而,在本案中,精神中心对原告的初步诊断缺乏足够科学性的具体表现。首先,出诊医生仅根据与原告的短暂对话即判定其患有人格障碍,未进行必要的走访和调查。其次,精神中心明知邱某与原告之间存在家庭矛盾,仅根据邱某提供的代诉及材料,在接触原告之前即对其产生了具有倾向性的预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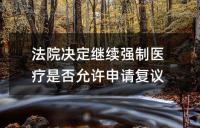
法院在强制医疗方面的决策流程以及强制医疗程序的特点和救济途径。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是上一级人民法院。强制医疗程序旨在保障公共安全并对精神病人进行必要的医疗,具有适用对象的有限性、决定依赖医疗机构的专业意见等特点。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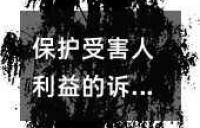
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诉讼时效起算标准。文章提出在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时,应当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更多地采用“知道”的标准而不适用“应当知道”的标准。考虑到专业因素,如某些药品的毒副作用损害难以被普通人了解,起算时间应考虑此特殊性。对于人身损害赔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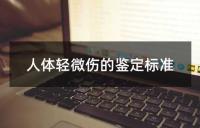
不同领域人体损伤鉴定的标准及其适用范围。包括轻微伤、轻伤、重伤、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等。文章详细说明了各类鉴定标准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涉及法律、工伤、职业病等多个领域。同时,文章还涉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和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等。
-

医疗事故认定依据中关于诊断失误的过错问题。文章详细阐述了问诊、检查、鉴别诊断等方面的过错情形,包括实施检查、未实施检查、体格检查、辅助检查以及鉴别诊断等方面的具体错误。同时,文章也讨论了治疗失误的过错,包括治疗方法选择、治疗时机选择以及用药的过错等。
- 医疗伤残鉴定的时机
- 眼睛轻伤二级标准
- 法医鉴定流程及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