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钱减刑会不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赔钱减刑”:在保障被害人权益的前提下的多赢举措
赔偿并非减刑的唯一条件
有关“赔钱减刑”的报道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担心是否可以通过金钱来减轻刑罚,是否富有的人可以比贫穷的人少受刑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通过赔偿来减轻甚至免除刑罚。赔偿并不意味着“赔了钱就不再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以这个案件为例,即使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如果他有足够的财产可以执行,仍然应该向被害人家属支付丧葬费、抚养费、赡养费、医疗抢救费和死亡赔偿金等。尽管在这个案件中,被告人的家属协助赔偿,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家人没有赔偿的义务。但是,如果家人自愿提供协助并取得被害人方面的谅解以及法院和检察院的认可,并且被告人本人没有赔偿能力,这是可以被允许的。这种自愿协助赔偿与无辜受牵连的非自愿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赔钱减刑”的价值判断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现代刑事追究模式进行反思,意识到过分强调公诉制度导致对犯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矛盾遗忘,尤其是对被害人感受和利益的忽视。因此,出现了从“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的转变,旨在通过调解、道歉、真诚悔过、积极赔偿等方式,恢复被害人与犯罪人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也在试行刑事和解和积极赔偿受害人等制度。这些做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理念,有利于推动和谐司法。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曾强调:“要注重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重要作用,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配套措施的完善
为了使“赔钱减刑”得到健康发展,我们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确哪些犯罪可以通过积极赔偿减轻处罚,哪些犯罪应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对于轻微故意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等,可以适当将赔偿与量刑挂钩,但对于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暴力犯罪,原则上不应实行赔偿减刑。其次,法官在具体判案时,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赔偿问题。赔偿是被告人悔过的表现,接受赔偿也是被害方在某种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体现。这个过程有时不容易实现,像本文开头的案例就是经过法官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细致调解才达成的。因此,需要在调解方法、程序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既防止强行将结果加于一方,又防止因调解不成而失去耐心。最后,应将被告人赔偿与国家补偿两项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目前,我国正在尝试建立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但这是否会导致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属寄希望于国家补偿而放弃接受被告人的赔偿,从而既不能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也不能得到补偿,需要进一步研究。
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花钱”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可以“买刑”,但这种“买刑”决不是金钱万能的结果。它是在国家公权力的主导下,以促进被害人权益保障和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为前提的一个多赢举措。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可以防止贫穷的人比富有的人多受刑罚。
-

职务侵占罪的刑罚问题。对于金额巨大的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者将面临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可能会被并处罚没收财产。文章还提到了职务侵占罪犯减刑和假释的限制,根据不同的罪行和刑期,执行时间和减刑幅度也有所不同。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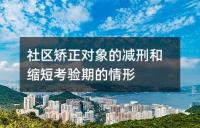
社区矫正对象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的减刑和缩短考验期的相关情形。符合遵守社区矫正管理规定、表现出悔改并积极回报社会等情形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减刑并缩短考验期。对于判处缓刑的社区矫正对象,建议修订刑法,规定在缓刑期间接受教育改造并表现良好的可以减刑,并相应缩
-

罚金作为刑罚的利与弊。罚金有其优点,如避免交叉感染、有利于犯罪人改造、增加国库收入等。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如因贫富差异导致的不公正、罚金执行难等问题。对于家庭困难的罚金减免,是被判刑分子在执行期间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可适用的减刑措施。减刑后的实际执行刑期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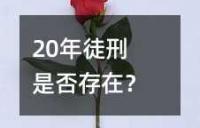
现行刑法下有期徒刑的相关情况。有期徒刑通常是数罪并罚或死缓、无期徒刑转有期徒刑后的结果。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若能表现出良好行为、立功表现,可获得减刑。有期徒刑的刑期相对较长,但会根据犯罪分子的表现与立功情况有所变动。
- 法院罚款不交不能减刑的相关法律知识
- 只有认真遵守监规和悔改表现吗?——关于减刑的法律规定
- 被判拘役缓刑后是否有减刑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