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辩护意见书中的辩护策略是什么

单位犯罪构成要件的考量
如果控方以自然人犯罪进行指控,那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能否构成单位犯罪。在双罚制的情况下,单位犯罪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被追诉人是否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需要进一步分析。
此外,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对责任人的处罚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较轻,故即使不能构成犯罪,也可取得罪轻辩护的效果。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或是二者均可,目前仍有争议,但司法实践当中较为接受的是过失说。过失说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时,对于行为所持的心态是故意,但对环境污染危害结果所持的心态是过失;如果对结果也持故意态度,那么就不能作为污染环境罪处理,而一般会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处理。无论是故意说还是过失说,都要求行为人明知污染后果会发生。然而,即使行为人以不明知作为抗辩理由,司法机关也可以轻易使用推定明知,即“应知”来反驳,甚至使用严格责任理论来实现指控目的。因此,主观要件上的辩护力度难以做强。
污染环境罪的客观行为要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污染环境罪的实施行为是指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的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对于违法性的辩护策略,一般情况下很难构成有效辩护,故辩护策略主要应围绕有无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和行为对象是否属于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这两点展开。
关于实施行为的辩护策略,污染环境中的实施行为一般表现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联的行为,因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广。辩方在此环节中,一定要深入了解案件相关背景知识,重新审视控方认定的实施行为,以及与污染物的监测数据、污染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行为对象的辩护策略,应审查据以入罪的染污物是否符合相应标准当中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入罪标准,污染物的种类并不相同。作为辩护策略,就应当审查据以入罪的染污物是否符合相应标准当中的范围。
污染环境罪的危害后果要件
从污染环境罪基本罪状表述来看,危害结果是要件之一,因此,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罪是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或危险犯。行为后果仍然是定罪量刑的首要考量因素。辩护策略应重点围绕危害后果的评价是否正确、后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展开。对于两高解释中关于加重处罚的情形,应审查其是否符合明确具体的数量标准,对于使用评估报告作为损害后果的认定,应严格审查其证据效力和科学性。
-

污染环境罪的故意方面规定,包括主观罪过形式、污染环境结果的认定以及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的构成。文章指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对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能够预见。同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侵犯了国家、单位和公民的环境权益,犯罪
-

环境污染罪的判定标准,区分了污染环境罪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特点,详细描述了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和客观要件。内容包括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和环境污染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文章指出犯罪行为的构成必须违反国家规定,并包括排放、倾倒和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
-

油烟污染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关于油烟净化设施和餐饮服务项目设置的规定。同时,文章还涉及污染环境罪中律师的作用以及油烟排放的监管部门。油烟污染问题的执法权限归城管部门,但由于技术设备等限制,市民可先向环保部门反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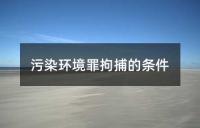
本条和本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散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污染环境罪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罪名做出补充
- 污染环境罪立案标准
- 污染环境罪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
- 污染环境罪故意犯罪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