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与道德爱情

禁止婚姻当事人索取财物的合法性问题
婚姻基础的讨论
禁止一方当事人借婚姻索财的规定在法律中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立法倾向。这似乎要求所有的婚姻当事人在建立婚姻关系时完全不考虑经济因素,只以纯粹的爱情为基础。然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立法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也脱离了法律操作的实际需求。
婚姻自由和动机的关系
婚姻自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决定自己的婚姻意愿的自由。至于婚姻的动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法律无法追究,这只是一个道德价值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干预的范围。
婚姻法的人文关怀
法律规范的温情脉脉
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新婚姻法突出地反映了法律对人类关怀的一面。它不仅触及到人的道德准则、自律规则,还触及到情感世界。通过大量不容选择的强制性规定,新婚姻法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导到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轨道上。这些规定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所认可。公民只能选择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而不是选择是否遵守这些规定。婚姻法将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领域纳入法律的管辖,例如将“忠实”作为婚姻的首要义务写入法律条文中。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夫妻间的不忠实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走向解体,也不能认为婚外性行为就一定需要刑法制裁。这些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更多的人选择在“城外”生活而不愿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果不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也对社会整体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离婚自由的争论和立法进步
婚姻自由原则的两个方面
婚姻自由原则由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构成。结婚自由是指建立婚姻关系的自由,而离婚自由是指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结婚自由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条件,而离婚自由则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离婚自由使得不幸的婚姻得以解除,为建立幸福的婚姻创造条件。没有离婚自由,就无法实现完全的结婚自由。
离婚自由的发展
相对于结婚自由而言,离婚自由经历了更多的困难和矛盾才逐步建立起来。婚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禁止离婚主义、限制离婚主义,到如今成为主流的自由离婚主义。自由离婚主义越来越强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尊重婚姻关系的本质。这代表了婚姻法律制度的先进化和文明化,也是我们追求更完善婚姻自由的动力。近期,针对离婚自由是否应进一步限制的争论,一方面认为离婚自由导致草率离婚,离婚率急剧上升,对社会稳定不利;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限制离婚自由就是限制结婚自由,是婚姻制度的倒退,限制离婚自由只会使婚姻当事人的矛盾在旧有体制下无法得到舒解,更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事实上,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离婚自由的限制并不是越来越多,而是逐渐放宽的过程。然而,这场争论不仅展示了人们对婚姻自由的不同看法,也揭示了婚姻家庭制度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个人意愿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在两性关系中,国家应扮演何种角色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首次规定了“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这一条款解放了中老年人头上的新束缚和经济上的顾虑,为人们在中老年时期的婚姻自由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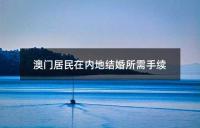
澳门居民在内地结婚的流程与规定。需遵守中国法律,提交相关证件和证明,询问结婚意愿并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宣读声明书后,登记员审查材料并颁发结婚证。此外,结婚登记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国家对婚姻关系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原则等。登记机关为各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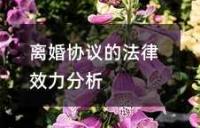
陈彤和其丈夫签订的一份惩罚性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该协议旨在约束双方,限制离婚权的行使,被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和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定为无效。文章强调,我国婚姻法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夫妻双方有权自愿离婚,并依法协商处理财产分割等问题。而该协议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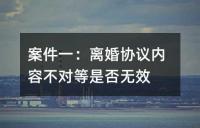
两个离婚协议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中,协议内容存在不平等条款,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被认为是无效的。第二个案例中,关于“净身出户”的协议,视情况而定。女方放弃工作的条款属于道德约束,不属于法律规范调整范围。而关于婚外情导致的净身出户约定,在夫妻自愿签订且不
-

我国婚姻法中关于离婚诉讼的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由权利,包括结婚和离婚自由,且离婚可通过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方式来进行。协议离婚需双方自愿并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诉讼离婚则是一方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审查后如认定感情破裂会判决离婚。同时,国家严厉打击
- 结婚合意的法律要求
- 结婚登记机关的职责和流程
- 婚姻自由的法律意义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