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交通事故调解协议的效力

对本案中的调解协议的司法实践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调解协议属于行政调解性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然而,在本案中,损害赔偿协议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的,而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因此,交警管理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协议属于行政调解性质,不具备民事合同效力。因此,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要求履行调解协议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实际损失作出判决。
第二种意见: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
根据第二种意见,王某作为侵权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公安交警主持的调解协议只要不是强制性的,只要是张某和王某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就具备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法院应认定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并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
作者观点:同意第二种意见
作者认同第二种意见,即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在本案中,调解协议涉及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问题,明确了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虽然公安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没有民事强制执行权,但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救济的方式请求对方履行,就像不履行合同约定一样。
此外,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协议本身表现出的性质来认定,不应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限制。如果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处理其他主体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认定其效力,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

交通事故调解书的必要性及其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文章介绍了调解书应包含的内容,如依据、基本事实、损失情况、损害赔偿项目和数额等。同时,文章还详述了交通事故认定中的时间、地点、当事人身份和联系方式以及机动车牌号和保险凭证号的确认方法。最后介绍了交通肇事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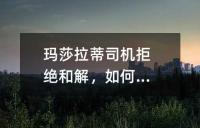
玛莎拉蒂司机拒绝和解的情况。在我国,刑事和解需双方自愿,如一方拒绝,司法机关应及时审判。对于醉酒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基于当事人的行为及过错程度。如果当事人逃逸,将承担全部责任。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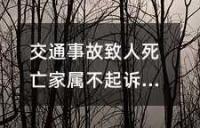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后家属不起诉的法律处理方式。涉及诉讼时效的影响和责任认定问题。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按过错程度承担责任。家属不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将无法主张赔偿,但肇事者仍需承担刑事责任。
-

原告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身体受伤和财产损失,向被告提出具体的赔偿要求。原告在上班途中被被告驾驶的车辆撞击,导致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自行车严重损坏。经过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认定,被告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和精
- 上班发生交通事故员工次责可以认定为工伤吗
- 夜间开车使用远光灯引发的责任问题
-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时间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