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摘要: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关键词:环境问题环境犯罪差异性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原则非刑罚制裁加快西部地区开发,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国家把发展的重心向西部地区转移,给我国西部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我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因此,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是整个西部地区开发建设中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刑法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当关注和思考这种重大课题。当前,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环境保护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环境保护立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学者倡导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但在针对环境犯罪问题上,却有犯罪化”刑罚化”甚至重刑化”的倾向,有的国家还规定了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西方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在刑法典、行政法规中规定或增设了刑事制裁条款,将那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惩治,突显国家以刑罚手段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我国1997年刑法典突破了以往我国环境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法条14个罪名。立足我国刑事立法的上述规定,结合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西部环境日渐恶化的趋向,笔者就西部大开发中环境犯罪适用刑法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一、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1.差异性原则。差异性原则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在对西部开发中的环境犯罪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一些不太明确的问题作出解释时,比东部或其他生态环境条件良好的地区采取更加严厉的标准。这是基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本身又具有十分脆弱的特性的考虑。因此,在关于惩治环境与资源犯罪的条文中,有许多诸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量较大”、数量巨大”等情节及后果的规定,国家立法机关或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时,针对西部生态环境应当比较严厉。例如,关于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中的数量较大的起算点,1987年9月5日两高《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分别规定了具体的标准,即在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2-5立方米或幼树100-250株;滥伐一般掌握在10-20立方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按林区的1/2计算)。为了因应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凡发生在西部地区盗伐、滥伐林木的案件,林区执行的标准可降格适用东部地区非林区的标准,非林区的标准相应作进一步下调。有人担心,在认定环境犯罪中,坚持东西部差异原则,势必会限制西部经济的发展,因而会从根本上阻碍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种担心是善意的,但却是不必要的。理由如下:其一,这是对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作了不正确至少是不全面的理解。因为西部大开发主要由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改善西部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四个部分组成,改善西部环境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从严惩治西部的环境犯罪不乏政策依据,是西部大开发的应有之义。也只有大力惩罚环境犯罪,保护、改善西部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加快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主要授予检察院、环境行政机关、环境团体或个人等主体。在欧美国家,检察院被视为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而中国的地方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认可了检察院作为原告的身份。然而,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只能进行有限的事后救济,其监督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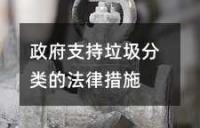
政府如何通过法律措施支持垃圾分类和处理。政府可以在小区建立垃圾分类设施,设立垃圾分拣处理站,吸纳就业并促进垃圾分类。同时,政府可限制过度包装和未经处理的蔬菜进入市场,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这些措施旨在有效应对垃圾问题。
-

目前关于疫苗案的刑法定性,主要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和故意杀人罪几个罪名上。某全国著名的疫苗案,被警方提请逮捕时,对外公布的罪名是生产、销售劣药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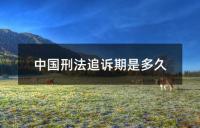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第八十八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在一种犯罪有几个量刑幅度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犯罪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长短,即
- 数罪并罚是指什么,数罪并罚的适用规则是什么
- 数罪并罚的刑期规定是什么
- 虚假出资律师办案技巧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