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侵权研究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解释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赋予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的一项新的“专有权利”。
它原本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而产生的,但网络技术的复杂性却又使它在现实中的适用远较传统“专有权利”困难。
在过去的两年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正东、华-纳和**唱片公司对chinamp3.com网站提起的三起诉讼作出的结果相同,但理由迥然相异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对“**唱片公司诉济宁之窗信息公司案”所作出的《批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音乐公司诉百度案”所作的一审判决以及正在审理之中的“**音乐公司诉飞行网案”均在司法界和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这说明对什么是“通过网络公开传播作品的行为”(以下简称“网络传播行为”)、何种行为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或间接侵权以及如何认定相关行为人“主观过错”等一系列问题尚缺乏统一认识,这自然会妨碍在网络环境中充分地保护著作权并维系权利平衡。
为此,本文试剖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内容并对“网络传播行为”加以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认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特别是间接侵权的标准,为法院对此项权利的正确适用提供参考。
二、界定“网络传播行为”是认定相关侵权行为的前提
著作权法规定“专有权利”的意义和目的在于控制特定行为。如果某种特定行为落入了某种“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则他人在没有法律特殊规定(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的情况下,擅自实施这种特定行为就会构成对此种“专有权利”的直接侵权。[1]例如,“表演权”控制公开表演或公开播放被录制的表演的行为,除了“免费表演”等有法律特殊规定的“公开表演”行为之外,对作品进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公开表演”即构成直接侵犯“表演权”的行为。与此相适应,各国著作权法定义“专有权利”的方法,就是对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加以界定。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的《版权法》首先在“定义”条款中对各种特定行为加以界定,然后再在“专有权利”条款中从正面规定版权人享有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专有权利”,或从反面规定何种特定行为受到“专有权利”的控制。[
其他没有在著作权法中单独设立“定义”条款的国家,则都在规定各“专有权利”时明确地划定受控制的特定行为,如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著作权法》就是如此。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规定“专有权利”,对受该权利控制行为的界定都是法院正确适用该权利的关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法院对于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的判断。如果一种行为根本不在某种“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之内,则他人实施这一行为不可能对其构成“直接侵权”。此时只能考察行为人是否在具有“主观过错”的状态下帮助或引诱他人实施了“直接侵权”,从而构成“间接侵权”。反之,如一种行为本身受到某种“专有权利”的控制,则他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未经许可地实施这一行为当然构成“直接侵权”,此时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与认定“直接侵权”无关,只影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3]
因此,要正确地认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网络传播行为”。没有对这一行为的清楚界定,对相关侵权行为的认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目前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之所以会对一系列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诉讼产生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网络传播行为”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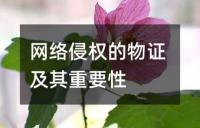
网络侵权案件的物证及其重要性。网络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主要侵犯名誉、隐私、肖像和财产权等民事权益。处理网络侵权需要有充分的物证,但数字化技术使得网络证据认定困难。网络侵权区别于传统侵权,包括认定难度、侵权主体、后果、司法管
-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侵权内容”指权利人认为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删除改变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最高人民
-

电子书版权保护,适用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通过这种无限制地复制和传播,电子书版权所有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而侵权人为侵权所付
-

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往往会将被告的主体性质区分为ISP或ICP,并据此来确定被告在侵权行为中的地位以及应否承担责任。内容即作品,未经许可直接提供内容,将其上载到互联网的,其间必然发生复制行为,即使不规定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可以认定内
- 常见的软件侵权盗版行为主要有哪些
- 网络侵权法律规定
-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问题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