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口提出要同伙抢一个手机,言语唆使属于帮助犯还是共犯

随口提出要同伙抢一个手机,言语唆使构成帮助犯还是共犯
一、基本案情
2012年4月,文某、李某、朱某、冯某等人在一起,朱某提出要去抢劫他人财物,文某、李某表示同意,冯某因自己的手机不好用,便要求朱某他们抢一个手机给自己。随后,四人一起至某中学附近巷口。在该巷口,文某等三人采取殴打、用砍刀威胁、语言恐吓等手段,抢劫被害人赵某等人手机二部、现金若干。期间,冯某并未参与实际抢劫行为,而在附近等待。抢劫所得手机一部由朱某赠与冯某,其他财物由朱某等三人平分。
二、案件分析
本案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根据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刑法理论将共同犯罪分为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三种形态,教唆犯与帮助犯亦称之为狭义的共犯。
共同犯罪中,正犯是与狭义的共犯相对的概念。原则上,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现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是正犯,此外的参与者都是共犯。
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要以认定正犯为核心,狭义的共犯的认定依赖于正犯的认定,只有认定了正犯,才能进一步认定教唆犯与帮助犯。在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只要能认定正犯的行为是由教唆犯的行为所引起,就能肯定教唆行为的成立;同样,只要能认定某人的行为对正犯的行为起到促进作用,就能肯定帮助行为的成立。
本案中,文某等三人采取殴打、持刀威胁、语言恐吓等手段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即属于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现了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构成要件,是抢劫罪的正犯。
三、争议焦点
在认定文某等三人构成抢劫罪正犯的基础,对于冯某是否构成抢劫罪及在抢劫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如下争议:
(一)冯某行为不够成抢劫罪。
冯某未直接实施抢劫犯罪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正犯,仅仅在文某等三人预谋时,要求三人为其抢劫一部手机,其行为既不符合教唆犯也不符合帮助犯的构成要件。
(二)冯某行为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属于教唆犯。
根据刑法理论,故意唆使并引起他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是教唆犯。本案中冯某在文某等三人预谋时,要求三人为其抢劫一部手机的行为属于教唆犯。
(三)冯某行为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属于帮助犯。
帮助正犯的,是帮助犯。帮助犯对正犯的行为起促进作用。冯某要求三人为其抢劫一部手机的行为属于帮助犯。
四、作者观点
作者认为冯某行为构成抢劫犯的共犯,属于帮助犯。
(一)首先,冯某行为不构成教唆犯。教唆行为的特点是使他人产生事实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故在被教唆者已经产生了该意思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成立教唆。本案中,文某三人已经产生抢劫的意思的情况下,冯某要求顺便帮其抢一个手机的行为,冯某的要求未超出三人抢劫的意思范围之外,故不成立教唆犯。
(二)一般来说,帮助行为是使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更为容易的行为。帮助行为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前者是指提供犯罪工具、犯罪场所等物资性的帮助行为,后者是指精神上的帮助行为,如提供建议、强化犯意等等。
本案中,冯某的行为,虽然未对文某等人的抢劫行为提供有形的帮助,但是其要求对文某等人的犯罪意思起到了强化作用,属于精神上的帮助行为,构成帮助犯。
刑法之所以处罚帮助犯,是因为帮助行为通过正犯促进了对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利益的侵害,因此,帮助行为与正犯的行为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这就要求帮助行为给正犯以心理的影响或者物理的影响,从而使实行行为更为容易。
本案中,冯某的行为强化了文某等三人的犯罪意思,对三人实施抢劫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其行为和三人的抢劫行为与结果直接具有因果关系,故应当以属于抢劫罪的帮助犯。
-

公司逃税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当单位经过组织策划实施偷税行为时,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文章还详细阐述了逃税罪的构成要件、刑罚、扣缴义务人的责任以及多次实施逃税行为的处理方式,同时提及了补缴税款和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关
-

帮助凶手逃走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根据刑法规定,帮助凶手逃走可能构成窝藏罪,如果事前与凶手通谋则视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需要满足条件,包括共同犯罪人必须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以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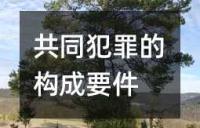
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主体要件要求二人以上,包括多个自然人、单位以及自然人与单位的共同犯罪。客观要件指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包括共同作为、共同不作为以及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等。主观要件则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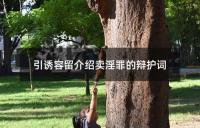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辩护观点。文章认为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且作为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处罚。文章详细阐述了被告人的行为特点、主观态度以及未成年人身份等因素,并希望法庭能够依据相关法律对被告人进行适当惩罚,同时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惩罚为
- 多人实施轮奸的法律处罚
- 主犯不承认证据不足从犯怎么认定
- 偷盗罪从犯没有收益怎么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