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的立功表现都有哪些

一、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罚执行期间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检举、揭发监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
(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
(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
总之,立功即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行为,上述立功表现是相对独立的,只要罪犯作出其中一种即可认为具有立功表现而可以获减刑奖励。
二、立功表现的前提条件
关于立功表现,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1. 是否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
一般情况下,立功表现常以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但并非是立功表现的必要条件。立法者注重罪犯的客观行为表现及其有效性,只要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具有立功表现,就可以减刑。有立功表现的人通常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但也不排除没有这种前提的立功表现。因此,刑法规定“可以”减刑。
2. 是否必须以有悔罪为前提?
法学界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立功除了要有客观表现外,主观上必须有真诚悔罪的态度,否则不能构成立功。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况各异,立功和悔改并不完全一致,悔改的罪犯未必有立功表现,有立功表现的罪犯也未必就一定悔改。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这符合刑事立法原意和相关刑事政策。虽然一般来说,立功常是在悔罪思想支配下产生的突出表现,但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有些平常表现一般的罪犯在关键时刻可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些罪犯,虽然他们尚未完全彻底悔改,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减小了人身危险性,同时通过他们的善行也可以感染他人,减少他人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对这样的罪犯予以奖励、适用减刑是符合刑罚执行政策的。
三、重大立功表现
刑罚执行制度上的重大立功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作出的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贡献的行为,是“应当减刑”的根本性要件。起初,“重大立功表现”是作为对有期徒刑犯减刑幅度予以例外宽大的一个条件。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确认了这一规定,并将“重大立功表现”适用范围扩展至管制犯、拘役犯等。
关于“重大立功表现”,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1. 如何理解“重大”?
“重大立功表现”与“立功表现”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程度上,即罪犯所为的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益程度不同。前者远远高于后者,是一般犯罪分子无法达到的,例如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或检举监内外重大犯罪活动。对于“重大”的标准,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重大立功”认定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罪或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不能将“重大立功表现”泛化为一般犯罪分子稍加努力即可达到的行为表现。
2. “重大立功表现”是否必须以罪犯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为前提?
对此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重大立功表现”不同于“立功表现”,罪犯应当减刑的首要条件必须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此仅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不构成必须给予减刑的充分条件。否定说认为,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就能构成“应当减刑”的充分条件,就像“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并非“立功表现”的必要前提一样。
在新的历史时期,监狱执行刑罚的首要任务是“矫正行为”还是“改造思想”的问题。笔者认为,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仅靠有限的刑期不可能完成,要求监狱机关一家承担也是困难的。法律规范的是人的行为而非思想,监狱的首要任务是矫正罪犯的行为而非改造罪犯思想。因此,使罪犯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能够按照社会行为准则从事各项活动,就可以认为达到了改造罪犯的目的。当然,矫正行为的重要性并不否定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够既改造思想又矫正行为是最佳目标。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侧重或首要价值取向。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对于没有悔改但有立功甚至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是否应减刑的疑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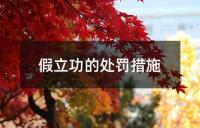
假立功的处罚措施。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伪造犯罪嫌疑人立功材料造成假立功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相关人员将受到刑事处罚。具体处罚措施包括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最高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职务侵占罪的刑罚问题。对于金额巨大的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者将面临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可能会被并处罚没收财产。文章还提到了职务侵占罪犯减刑和假释的限制,根据不同的罪行和刑期,执行时间和减刑幅度也有所不同。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以
-

有期徒刑的期限和刑度问题。除了规定的期限范围外,还有死缓执行期间的重大立功表现和多罪并罚的特殊情况。刑法分则对有期徒刑的刑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形成了多个刑度格。有期徒刑的执行场所包括监狱和其他场所,罪犯需参加劳动改造和接受教育。劳动改造具有强制性,而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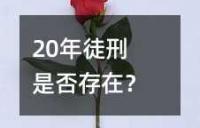
现行刑法下有期徒刑的相关情况。有期徒刑通常是数罪并罚或死缓、无期徒刑转有期徒刑后的结果。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若能表现出良好行为、立功表现,可获得减刑。有期徒刑的刑期相对较长,但会根据犯罪分子的表现与立功情况有所变动。
- 无期徒刑和死缓的区别及刑罚变更
- 减刑的条件和限度
- 重大立功表现量刑标准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