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埋藏物归属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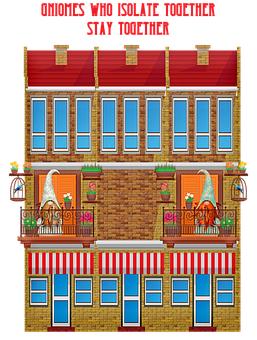
一、民法的埋藏物归属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对上缴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3条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能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我国《物权法》第114条规定:“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113条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公有主义的立法例,发现人不得取得所有权,只可能受到一定的表扬或物质鼓励。
二、埋藏物的特点
埋藏物是成就发现埋藏物的条件之一,所谓发现埋藏物是指隐藏于他物之中,而其所有人不明的动产。通说认为,埋藏物具备三个特点:
其一,埋藏物应为动产。埋藏物公限于动产,如金银财宝、珍奇古玩等。古代房屋或城市因地震、火山、泥石流等事变被埋没于地下,已成为土地的一部分,不构成埋藏物。
其二,埋藏物应为埋藏的物。所谓埋藏,是指包藏于他物之中,难以从外部目睹的状态。包藏物一般为土地,但不一定限于土地,建筑物或动产均可以为包藏物,如将古玩字画藏在墙壁中,将珠宝藏在电脑的机箱中,至于埋藏的原因,究竟是由于人为的事实还是自然事件,则在所不问。另外,德国民法、瑞士民法都要求埋藏物以经过长时间的埋藏为必要。我们认为,认定埋藏物主要应依据其是否处于“埋藏”状态,至于埋藏的时间长短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况且,如何认定“长久”也相当困难,因此埋藏物不以长时间埋藏为必要。
其三,埋藏物的所有人不明。所谓所有人不明,是指埋藏物并非无主物,但不知属于何人。如果根本没有所有人,应当适用无主物先占的规定;如果有明确的所有人,则应适用拾得遗失物的规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均不属于埋藏物。至于如何判断“所有人不明”,则应“就物的性质、埋藏的状态、埋藏的时日等客观情形加以认定”,而并非以发现人的主观认识为判断标准。
三、埋藏物的发现
所谓埋藏物是指埋藏于土地及他物中,其所有权归属不能判明之动产。此项概念,须从下述四点加以进一步解明。
其一,埋藏物须为动产。此所谓动产,通常系指金银财宝。
古代房屋或城市因地震、火山爆发等事变被埋藏于地下而成为土地之一部者,不构成埋藏物。并且,人类之遗骸亦非埋藏物。但是,有考古价值之木乃伊,应认为系埋藏物。另外,埋藏物于罗马法上虽以高价物品为限,但十九世纪以来的各国立法及实务均不以此为必要,我国亦应作相同解释,当无疑义。
其二,须为埋藏之物。所谓埋藏,系指包藏(隐藏或埋设)于他物之中,不易由外部窥视或目睹之状态。他物又称为包藏物,主要系指作为不动产的土地。但其他不动产如建筑物及动产,亦可成为包藏物。例如墙壁或天花板中隐藏之物,屏风中挟藏之物,衣襟中缝入之物,皆得成为埋藏物。至于埋藏的原因,究出于人为或自然,皆所不问。埋藏时间虽通常为久经年月,但不以此为必要。
其三,须为所有权归属不能判明之物。埋藏物于性质上非为无主物。
无论其过去曾为谁所有,抑或现在其仍由继承人继续性所有,均在所不间。但在现实上,该埋藏物所有仅于归属上须是不能判明,则是无疑因此,被发掘的古代人类的占坟与其中所藏置的物品及古生物化石,系无主物,而非埋藏物。至于所谓现实上所有权归属不能判明,则应就物之性质、埋藏之状态、埋藏之时日等客观情形予以认定,而非以发现人之主观认识为判断标准。例如甲为避盗,将若干金银藏于其屋墙壁,甲死亡后,该房屋被辗转出售。若能辨明金银为甲所藏,则应归其继承人所有,倘不能辨明时,则属埋藏物。
-

行政处罚的追责时效相关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行政机关不再追究行政法律责任。追责时效的设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行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机关加强执法监督和追责力度。但追责时效也有其限制,在特殊情况下需依据
-

表见代理与善意取得两者之间的区别。表见代理和善意取得都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但二者在相对人的注意义务、适用场景及构成要件等方面存在不同。表见代理涉及代理行为的外观,其构成要件包括无权代理、客观上的代理权理由等,但存在可操作性不足和善意判断不明确
-

协商分期还款或以物抵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只要在判决宣告前,被告人与自诉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将占有的财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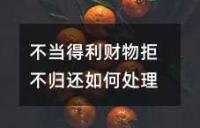
不当得利财物拒不归还属于违法,若数额较大,有构成侵占罪之嫌。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
- 发现埋藏物据为己有与不当得利的区别是什么
- 侵吞遗产罪如何判刑
- 人们捡到无主物如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