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与拆迁的利益冲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土地需求越来越大,各地政府不断加大征地和拆迁速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居民房屋拆迁,成为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因为征地和拆迁而引起的利益冲突越发明显。
有关资料预计,1999-2010年,耕地减少面积至少1.6亿亩,近3000万农民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伴随着土地的流失,依附土地的各种权益也随之流失。在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安置的实施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状态。这种弱势具体体现于:首先农民对征地的前期工作参与不够,对征地、工程建设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被征地农民对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由于“信息不对称”,缺少民主程序、缺乏透明度,也是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有抱怨、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其次申请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裁决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难以实行;最后在补偿费用的分配机制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乡村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被安置的农户的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征拆矛盾的症结,除了征拆双方地位的悬殊与不对等,还在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衡。土地转让产生了较大(或巨大)的收益,但在分享土地的转让收益或增值时,却往往忽视了被征地农民或被拆迁人的利益。仅仅给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规定的补偿,没有保障农民随土地增值而分享这种收益,引起了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对政府的不满。有关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政府和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之间没有实现公平交易,利益分配机制的缺失或未制度化,使得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不仅未能从城市开发中受益,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
此外,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了依附于土地的工作。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劳动的对象、工作的场所,农民只有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其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农民下岗”。根据我们对苏州、无锡、宁波等征地中失地农民的调查,失地农民再次就业率在25%左右。也就是说农民失地就意味着失业。而比失业更为严峻的一个问题则是,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长远收益,中国现行的农村养老制度也是基于土地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产权交易的规则是,农民决定是否放弃农的使用权,要考虑是否比他自用农地更“值",也就是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农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往往只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理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决定这种分歧存在的客观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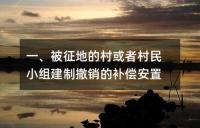
在征地过程中,被征地的村或村民小组建制撤销与不撤销的补偿安置问题。对于撤销建制的村庄或小组,提供了货币补偿和产权房屋调换两种选择。对于未转为城镇户籍的被拆迁人,可以在特定区域申请宅基地新建住房,并获得相应的货币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及相关规定也有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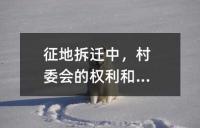
村委会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责。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有权协助政府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并反映村民意见,但没有土地征收、审批、收回土地使用权、代替村民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和私自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力。村民应了解村委会的权利和限制,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

商铺拆迁补偿的标准,包括搬迁前期和过程中的费用补偿、基于拆迁政策的奖励费用以及拆除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补偿。具体补偿包括机器设备调试修复等费用、速迁费及拆迁奖励等,且因拆迁导致的停产停业商铺将根据过渡期限给予相应补偿。因拆迁导致的商铺停租也将得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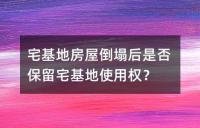
宅基地房屋倒塌后是否保留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如果房屋倒塌后超过两年未恢复使用,宅基地使用权将不再享有。但对于提问者的情况,其户口仍在农村,老宅虽然残破但仍未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其在拆迁征地过程中应享受相关补偿。因此,在涉及拆迁征地问题时,
- 征地拆迁费用属于地勘费用吗
- 拆迁对征地有影响吗
- 违法征地怎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