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案件的分类主要有哪些

土地纠纷案件的分类
一、集体与个人间的土地纠纷
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自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民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与村民集体订立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然而,由于合同订立时的法律、法规、政策尚未完善,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极为简单,甚至只是口头合同,或者村集体负责人未经讨论,私自将土地发包。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村民管理意识逐步增强,纠纷也随之出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合同内容过于简单,未能保障村民集体的利益,导致纠纷发生。
2. 没有书面合同,村集体要求完善合同,但承包金或使用年限难以协商一致,引发纠纷。
3. 合同订立时未告知村民发包情况,村民以合同未经法定程序讨论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提起诉讼。
4. 国有农场土地划拔后,农场职工未经农场方同意私自转包,农场按规定收回土地,引发纠纷。
5. 弃耕抛荒地未终止原合同的情况下,村集体另行与第三方签订新合同发包,引起原承包者与发包方违约的纠纷。
6. 合同期满后,承包者拒不交还原承包地,要求集体赔偿地上附属物或有关土地的投入成本,引发纠纷。
7. 以前村民集体将余留地和机动地交由村民使用,但双方未订立合同,也没有约定使用年限。后经村民集体决定收回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时,部分人拒绝执行决议,与村民集体发生纠纷。
8. 合同约定的条件过于苛刻,承包者一旦违约未能按时缴纳承包金或改变承包地用途,村集体以承包者违约为由意图收回土地,引发诉讼。
村民采取蚕食的方法占用集体土地,或者承包小面积土地后将周围空闲地不断开垦,长期侵占集体土地而引发纠纷。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许多村民私自开垦荒山、荒坡,使用撂荒地。村集体未及时制止这种行为。随着土地增值和村民组织的健全与规范,村组织决定收回这些原属于集体所有且未承包的土地,并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引发原使用者与村集体之间的纠纷。
纠纷还可能由于村集体领导更换,随意否认或变更原承包合同而引发。
当村集体将土地向外发包或将荒地用于合伙开发农业时,村民未提出异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土地投入的增加,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一部分村民因嫉妒而将村集体与承包者诉至法院,引发纠纷。
村集体领导在任期间采取互相勾结、欺骗等手段,违法将土地发包给自己,违反公平和合理原则,与村民发生纠纷。
二、个人与个人间的土地纠纷
个人承包集体土地后,经营有方,获得丰厚利润。其他村民受利益驱动,集体哄抢或霸占承包地,甚至采取多种手段故意破坏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承包合同无法履行。
土地权属界限不明,由于历史原因,使用权人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特别是一些离村较远的荒地和插花地,由离土地较近的农户进行开发和种植,随后产生效益,引发纠纷。
自留地和自留山的使用权争议。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我市,“祖宗地”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尽管经历了多次土地变迁,但农村土地“私有”现象仍然存在,自留山和自留地的使用仍处于解放前的状态。虽然村小组经历了第二轮承包,但仍未将这类土地纳入承包范围,仍由原使用人使用和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变化,农户之间、农户与承包集体之间因范围界线不清引发诉讼,而农户的使用基本上只是凭口头约定。
弃耕抛荒地被他人重新开垦使用后引发土地使用权之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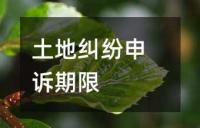
关于土地纠纷申诉期限和土地纠纷处理原则的相关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土地纠纷处理需依法进行,保护土地现状和合法权益,维护历史协议和乡规民约,合理处理无偿占有或平调引起的纠纷,保护原社队或个人的权益等。同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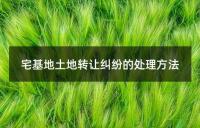
宅基地土地转让纠纷的处理方法。包括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协商不成可向受理机关提出处理申请或向上级申请复议或诉讼。同时介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在处理宅基地权属争议时,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村民合法权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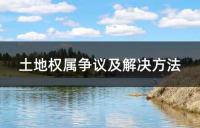
土地权属争议的定义及其分类,包括国有用地与农民集体之间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多类争议。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三级权属争议调处平台和联动机制,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强化争议调处工作的前期预防和排查,并注重人才培养和业务培训等措施来解决土地权属争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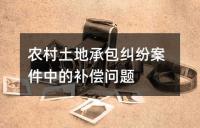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补偿问题。承包方有权请求发包方给付征收承包地的补偿费,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同时,对于流转承包地的补偿问题也进行了说明。文章还强调了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案件的重要性,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并处理好征地补偿
- 民事诉状
- 什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
- 工伤赔偿纠纷请律师收费标准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