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继承关系探析

引言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生命权是自然人最基本的人格权利。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不仅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带来财产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用、丧葬费用等已支出的费用,还应考虑到被害人健康生存所能获得的财产。此外,被害人的亲属由于被害人死亡而失去的抚养利益,也应得到补偿。这些赔偿内容可以纳入财产上的利益范畴进行具体分析。关于非财产上的利益,可以分为被害人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和死者亲属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各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不同,导致权利的归属也不同,因此在讨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时,需要从体系化的角度进行细致分析。
二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一) 立法现状
在我国,对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深入探讨,直到近年才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逐渐增多,理论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
回顾80年代以后我国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与立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阶段。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虽然未对致人死亡的情形做出具体规定,但从相关条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此问题非常关注。此后,《民法通则》公布实施,明确了身体伤害的赔偿范围,以及精神性人格权受侵害的损害赔偿。然而,《通则》存在一定的弊端,未对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进行规定,也未解决被害人死亡时赔偿金额不足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民通意见》于1988年通过,进一步解释了人身侵害中的赔偿内容,但仍未解决赔偿金额不足和被害人死亡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结果阶段。此阶段出台了大量的部门法、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首次在赔偿内容中增加了死亡补偿费。1993年,通过了《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前者提出了抚恤费的概念,后者首次使用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2000年,《产品质量法》大幅修改,删除了抚恤费的规定,增加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同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出现了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此外,还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具体规定了被害人死亡时的赔偿办法,使赔偿金额有了可预见性。
在司法解释方面,出现了一些仅适用于特殊领域的司法解释,如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和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解释,明确了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2003年发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对被害人死亡时的损害赔偿进行了具体规定。
(二) 问题
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制定是在摸索中前进的。虽然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进行了补充,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首先,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虽然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目的是扩大赔偿范围和金额,但由于未考虑各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和基础,导致法律不统一。其次,法律术语不统一。不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出现了抚恤金、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术语,造成概念界定的模糊。再次,缺乏与继承关系相关的讨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财产上的损失和非财产上的损失,但对于死亡补偿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 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一) 积极的损害
积极损害的赔偿
积极的损害是指被害人已经支付的费用,如医疗费用、丧葬费用和交通费等。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这些损害的赔偿是得到承认的。医疗费用和交通费是因为侵害人身权利而产生的支出,即使被害人死亡,相关的请求权仍然在被害人身上产生,然后由死者的继承人依照继承关系主张行使。关于丧葬费用是否属于积极的损害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被害人死亡时必然会有丧葬费用的支出,尽管这项支出是由加害人的侵害提前产生的,但这是任何人都必须支付的费用。因此,应该考虑这项本应由死者支付的费用是否应由加害人支付。
根据台湾地区的《民法》和德国、瑞士的法律规定,丧葬费用的请求权不受限制,直接承认了这一请求权。在日本法上,虽然民法没有对丧葬费用做出规定,但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在与被害人社会地位相符的合理范围内承认了这项赔偿请求。我认为,各国之所以做出上述规定和理解,是因为虽然一个人必须支付丧葬费用,但当被害人因人身受到侵害而死亡时,法律规定丧葬费由加害人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或慰藉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创伤。
逸失利益的赔偿
逸失利益是指被害人因受到不法侵害而死亡时失去的今后可能得到的利益。根据民法一般原理,逸失利益的赔偿请求权必须由被害人取得并确定。关于是否应该承认由死亡衍生出的逸失利益的赔偿请求权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被害人受伤和死亡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内或在被害人受到致命伤害的瞬间,赔偿请求权已经产生。另一些人认为,死亡是人身伤害的极端结果,对于死亡时的赔偿请求权应与对身体受伤时产生的损害请求权一样,承认请求权的存在。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根据均衡论,被害人在受伤时遭受的损失不可能超过被害人死亡时所遭受的损失。计算上来看,对重度伤害产生的逸失利益,只需将时间延长至被害人的平均寿命,即可视为死者的逸失利益。为了考虑被害人亲属的救济,这种逸失利益可以通过继承关系由死者的继承人获得。
然而,比较法中对逸失利益的继承性存在不同的做法。德国和瑞士的立法并未承认死者逸失利益的继承性,除非加害人已经承诺给予赔偿或被害人已经提起诉讼。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未承认逸失利益的继承性。日本法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逸失利益的继承性,但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承认了这项赔偿请求权。此外,在如何计算一次性支付死者逸失利益的问题上,日本的最高法院采取了Hoffmann计算法或Leipnitz计算法,为逸失利益的计算提供了明确的基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承认了死者逸失利益的赔偿请求权,也必须根据损益相抵的原则,在计算时扣除死者自身的生活费用。
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主要指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问题,在我国乃至比较法上引起了争议。精神损害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利益。本文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在广义说的角度上理解的。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主要包括对死者近亲属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对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和创伤的赔偿。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死者本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的抚慰。死者近亲属作为间接被害人,在心理上遭受创伤,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固有权利向加害人提出精神上的损害赔偿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相比,由于前者不具有客观性,难以具体计算,并且具有一身专属性,因此未经死者本人确定不可转换为金钱债权。一些国家的立法否认了死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转让性和继承性,但在加害人已经承诺给予赔偿或被害人已经提起诉讼的情况下除外。然而,这种立法模式受到质疑,因为被害人受伤和死亡之间的时间间隔短暂,有时无法请求赔偿。此外,获得加害人的承诺也不现实。因此,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不继承性在立法上是不合理的。德国在1990年废除了有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不继承性的规定,承认了由人身伤害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由继承人继承。这种更改在理论上有其利弊,可以从日本法中得到一些启示。
日本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问题
引言
在日本,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虽然理论界普遍认可该权利具有一身专属性,但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该权利的解除方式,这给予司法实践很大的解释空间。早期判决与意思表明继承说
早期的判决认为,被害人只要在死亡前做出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该权利即可转化为金钱债权,继而成为继承的对象。这种被称为意思表明继承说的做法在之后的一些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得到继承。判定被害人意思表示的标准
然而,关于如何判定被害人死亡前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判决始终未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判决认为某些高呼声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而有些判决则不承认这种意思表示。学者批评这种以被害人在危难时刻发出的呼喊作为判决的衡量基准,并指出这会导致不均衡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变更立场
在批判的影响下,日本最高法院在60年代末对立场做出了变更,并指出,只要不存在放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特殊情形,该请求权也可由死者的继承人继承。学界对继承性的否定态度
然而,大多数学者对这种全面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之继承性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质疑这种做法从精神赔偿费的性质、一身专属性以及死者亲属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角度。德国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问题
德国法与日本法的相似性
德国在1990年对民法典的条文进行了修改,删除了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继承性相关的内容,使得德国法与日本法的条文具有了相似性。德国判决的折中解决方法
德国判决采取了较为折中的解决方法,即在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期间从未苏醒,或完全丧失知觉及感知力的情况下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继承性。德国判决的问题
德国判决的这种做法似乎又会造成被害人即刻死亡情形下的不均衡问题。综合分析与讨论
理论上的困扰
即使立法承认了死者精神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仍会产生一些价值判断上的困惑及逻辑上的矛盾。消除理论困扰的关键
为了消除理论上的困扰,单独考虑请求权的继承性似乎难以寻找到更好的突破口。关键在于如何扩大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意义
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恢复被害人丧失的精神利益、填补作用和制裁作用。共同生活体的利益
被害人与其共同生活的人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应该将其共同利益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不承认死者死亡利益的继承性
不承认死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性,而扩大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可以解决理论上的矛盾。优点与整合性
这种做法可以使赔偿额符合均衡论的目的,解决逻辑矛盾问题,并维持法律内容和体系的整合性。结论
在我国的立法中,不应承认死者死亡利益的继承性,而应该通过扩大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来解决理论上的矛盾。这种立法模式可以从填补功能、防止商业化、维持整合性等方面带来优势。在制定民法典时,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进行综合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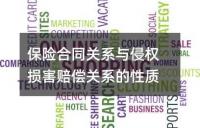
保险合同关系与侵权损害赔偿关系的性质。文中明确区分了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以及机动车方与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同时,详细阐述了受害人的请求权和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以及在不同诉讼情况下法院对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的处理方式。此外,文章
-

本案中,A公司与苏某家属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A公司支付给苏某家属50万元的赔偿款,但实际只支付了30万元。A公司以此为依据向B公司和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共同赔偿94万余元。一审法院判决B公司和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不服判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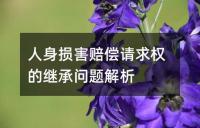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分析了近亲属赔偿请求权产生的条件和内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享有赔偿请求权的顺位按照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确定。在本案中,原告作为A的监护人只能保护A的合法权益,没有资格以监护人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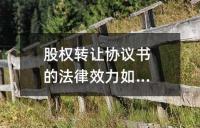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转让。民法典规定,只有财产损害能够转让,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专属性,只有受到人身伤害的受
- 不计免赔特约险详解
- 人身侵权求偿是否可以转让
- 行政赔偿实质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