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养关系和尽道德义务如何认定的

基本案情
原告和被告关系
原告江甲、江乙为二原告的子女,被告李丙为被继承人刘某的子女。
婚姻关系和约定
1981年,二原告的父亲江某与被告的母亲刘某结婚,双方均为丧偶再婚。在结婚前,江某与刘某约定,被告李丙与他们共同生活,而江甲、江乙则与祖父母一起生活。江某每年从收入中拿出400元给江甲、江乙的父母,用于二原告的生活费。此外,江某与刘某从事个体经营,收入丰富,并每年给予江甲、江乙1000元以上的钱以及服装和生活用品等,直到二原告19岁高中毕业找到工作为止。
继承处理
2001年,江某去世后,江甲、江乙与李丙、刘某协商处理了江某的财产继承问题。2005年11月,刘某去世,留下一栋价值约60万元的楼房、27万元的存款以及5万元的生活用品。江甲、江乙与刘某因继承纠纷将此事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他们的继承人身份并继承刘某的遗产。
分歧意见
在审理中,法院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
根据第一种观点,应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在未成年时期的生活费及教育费是由其生父江某与刘某共同支付的,这表明二原告与被继承人形成了扶养关系。尽管二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赡养义务,但考虑到被继承人和被告的经济条件较好,而二原告的经济条件较差,不足以认定二原告对被继承人的遗弃,因此,二原告并未丧失继承权。
第二种观点
根据第二种观点,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并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扶养关系,因此不符合继承人的范畴。被继承人在生前给予二原告生活费、教育费等,并不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基于与二原告生父的婚姻关系所自愿承担的道德义务。
法理评析
本案要确定二原告是否享有继承权,关键问题是弄清二原告与被继承人刘某是否形成法律上的扶养关系。即刘某在与二原告的父亲江某结婚后对二原告支付生活费、教育费等是否属于法律上的扶养关系。筆者认为,二原告与被继承人并未形成法律上的扶养关系,理由如下:
无法定抚养义务
首先,再婚的当事人对丈夫(或妻子)的未成年子女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再婚的当事人对丈夫(或妻子)的未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尽管通常情况下再婚夫妻与对方的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对另一方的未成年子女提供生活、教育费用并进行监护和教育,法律上认定这种情况形成抚养关系只是对事实的认可,这只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结果,而非法律上的义务。
未形成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
其次,被继承人刘某与二原告并未共同生活,即未形成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刘某在与二原告的父亲江某结婚时约定,二原告不与其共同生活,二原告的生活、教育费用由江某的收入支付。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刘某使用与江某共同财产为二原告提供了大部分生活和教育费用,但刘某一直未与二原告共同生活,也未表现出与二原告形成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
非抚养关系的必要条件
再次,承担未成年人生活和教育费用并非形成抚养关系的必要条件。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形成抚养关系的条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承担未成年人生活和教育费用并非形成抚养关系最本质的法律特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形成抚养关系的最本质法律特征应是意思表示、共同生活以及继父(或继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教育。例如,再婚夫妻即使实行约定财产制度,若未成年子女由其父亲(或母亲)承担生活、教育费用,但只要在一起共同生活,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实施了监护和教育工作,同样可认定形成抚养关系。因此,本案中被继承人刘某虽然承担了二原告在未成年时期的部分生活、教育费用,但这并非形成抚养关系的最本质法律特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
综上所述,尽管被继承人刘某承担了二原告在未成年时期的部分生活、教育费用,但这并非形成抚养关系的最本质特征和必不可少条件。同时,被继承人与二原告并未形成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为二原告提供部分生活、教育费用仅基于与二原告父亲的婚姻关系所自愿承担的道德义务,并无法找到法律依据要求履行这种义务。因此,法院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

附身份关系的赠与合同的有效性。依据合同法规定,该类合同一般是有效的,并受法律保护。合同无效的情形包括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赠与合同可附义务,但任意撤销需有限制,已转移财产权利的部分不可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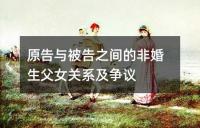
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非婚生父女关系及其争议。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抚养费、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并承担相关诉讼费用。被告与原告母亲存在亲密关系,导致原告出生,但自出生以来一直由母亲抚养,被告未履行抚养义务。因双方无法协商解决争议,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
-

离婚协议中赠与财产撤销的问题。在离婚协议中,夫妻将房产赠与子女是基于人身关系和照顾子女利益的道德性质。离婚协议不同于一般合同,具有强烈的人身关系属性,不应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的规定。夫妻一方不能任意撤销赠与,需取得另一方同意。任意撤销行为可能导致不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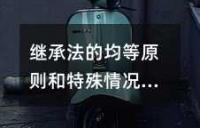
继承法中的均等原则和特殊情况下的遗产分配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同一顺序继承人应均等分得遗产,但生活有特殊困难或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可考虑多分或少分。小王的大哥因生活困难缺乏劳动能力,应获得更多遗产份额;而小王尽主要扶养义务并共同生活,亦可获得更多份
- 股份代持协议的合法性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组成
- 同居关系解除的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