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绝对外交豁免权是什么意思

外资豁免权的定义与原则
外资豁免权是指外交代表在驻在国享有的一定特殊权利和优待,包括对驻在国的管辖权的豁免。根据国际法和协议,各国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了保障和便利外交代表履行职务,互相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外交特权和豁免属于代表的国家,而非个人,因此个人无权自行放弃这些权利。
香港的绝对外交豁免权
绝对外交豁免权是指主权国在某一司法管辖区享有无条件的外交豁免权。
案例: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刚-果享有绝对国家豁免权
2011年9月8日,香港终审法院根据人大释法结果裁定刚-果胜诉,享有绝对国家豁免权。这意味着美-国公司不能在香港追讨刚-果的债务。
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中国中-铁提供开矿权,作为交换,中国中-铁在刚-果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高速公路、机场、医院和公营房屋等。然而,一家美-国基金公司以刚-果的债权人身份要求截取中国中-铁1.02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款来偿还债务。
刚-果认为,提供矿产给国营的中国中-铁,以换取基础设施投资,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香港法院无权对此进行裁决。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芮*牟接受了这一观点,判决刚-果胜诉,禁止美-国基金公司FLLC向中国中-铁追债。
然而,刚-果在原审时提出,即使主权国的国家行为说法不成立,刚-果在香港也享有「绝对外交豁免权」,即主权国在香港法院享有无条件的豁免权,使刚-果无需偿还债务。这一观点引起了香港律政司和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关注和支持。然而,稍后香港上诉庭坚持香港沿用普通法制度,认为这种交易不能获得绝对外交豁免,以2比1的判决推翻了刚-果的胜诉。
刚-果不服上诉庭的判决,向终审法院上诉,并要求终审法院就外交豁免权提请人大释法。这是香港回归近14年来,终审法院首次主动提请人大释法。终审法院颁布了关于刚-果债务诉讼的判决,裁定外国政府在香港法院享有司法「绝对豁免权」,同时提请人大澄清《基本法》第13及19条中有关「外交事务」的定义。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3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第19条则指香港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在有需要时,法院应取得行政长官请示中央人民政府后发出的证明文件,以文件内容作为判案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于2011年8月底在北京召开,听取了香港终审法院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债务引发的外交豁免权争议,并提请解释基本法第13条第一款和第19条的草案。会议一致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第一款和第19条的解释。释法通过后,香港需要遵循中国的决定,给予刚-果绝对外交豁免权。
-

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定义、范围及意义。这些权利旨在保护外交代表及相关人员在履行职务时的权益,包括人身和住所不受侵犯、免受行政和司法管辖等特权。特权和豁免权的适用对象包括外交代表、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国际会议的外国代表等也享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有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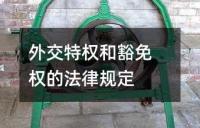
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法律规定。外交人员和某些外国组织代表享有不可侵犯权、司法豁免权等特权。我国法律规定了针对享有这些特权的外国人员、组织在某些情况下的民事管辖权。另外,还涉及民事诉讼时效和管辖异议复议的相关内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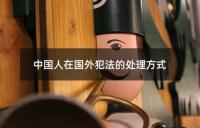
中国公民在国外犯法的处理方式。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犯罪发生地国法律优先处理,同时中国也会依照法律进行追究。对于不同刑罚,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外国人在国外对中国或公民犯罪也做了相关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则通过外交途
-

外交豁免权的定义和性质,以及它包含的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外交豁免权是各国授予外交代表的外交特权,旨在方便其履行职务。包括使馆财产和档案不受侵犯、外交邮袋不受开拆或扣留等。除外交代表外,其他特定人员也享有此权利。但外交代表若以私人名义从事商务等活动引起
- 法官是否享有豁免权
- 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含义及相关法律规定是什么
- 刑事辩护词范本怎么写才能从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