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村民破坏选举是否构成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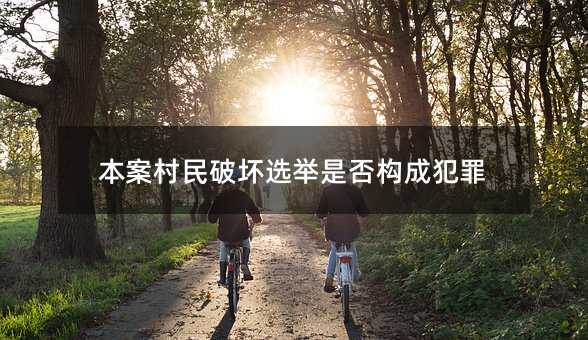
案情
2001年11月,某村举行第一轮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原村主任周某比另一位村主任候选人陈某少了200多张选票。犯罪嫌疑人张某(系周某亲戚)得知后,便请人伪造了该村选举委员会的印章和500张选票,在第二轮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时,趁工作人员不备,将其伪造的500张选票夹在正式选票中投入票箱,致使该村委会主任选举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破坏选举罪
有人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选举罪。根据该意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一种依法进行的选举活动,张某伪造选票并夹带进票箱的行为属于破坏选举的行为之一。尽管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对象不是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但从选举的重要性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来看,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应该被视为破坏选举罪,以维护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村民委员会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某些行政管理工作时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妨害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也构成破坏选举罪。
第二种意见: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
有人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根据该意见,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属于人民团体,张某伪造的村选举委员会印章属于人民团体的印章,因此其行为构成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
第三种意见:行为不构成犯罪
有人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该意见,破坏选举罪的构成要件规定是破坏选举的对象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而不包括村民委员会委员。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行为没有明文规定为罪,就不能处以刑罚。即使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适用类推,以破坏选举罪对此类行为进行定罪处罚。此外,村选举委员会并不属于人民团体,因此张某的行为也不构成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
评析
笔者原则上同意第三种意见,即对上述行为目前无法以犯罪论处。
根据刑法学的通说,犯罪行为的三个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明显的,但目前我国刑法无法找到对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的规定。因为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破坏选举罪,要么限定为违反选举法的规定,要么限定为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的行为。这样一来,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就钻了法律的漏洞。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也没有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规定刑事责任的条款。该法只规定,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导致当选资格无效,并未规定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仍然找不到依据。
-

犯罪构成与违法性质的区别与联系。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符合《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而违法是指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一定构成犯罪。犯罪必然是违法的,但并非所有违法行为都构成犯罪。因此,需准确理解和运用这两个概念,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

犯罪中止即使没有导致实际伤害是否算犯罪的问题。犯罪中止虽然未造成实际伤害,但已构成犯罪,因为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犯罪中止的行为显示出一定的犯罪意图和肇始行为,只是在行为人主观上自动放弃或有效防止结果发生才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
-

犯罪构成体系的概念及其特征表现。该体系包括不同学派的独特观点和评价体系,涉及主体、客体、主观和客观等要素。犯罪构成特征包括行为人的资格、行为对象、主观和客观要件的综合,以及违法性和责任的法律定位等关键要素。此外,文章还介绍了标准的犯罪构成和派生的犯罪
-

犯罪构成的三大显著特征,包括主体、侵害对象以及客观和主观要素之间的有机组成,是违法性与责任性的法律标识,也是判定犯罪行为的法律依据。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要件。犯罪主体是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或法人,主观方面探讨犯罪主体的心
- 犯罪构成特征是什么意思
- 犯罪构成的内容有哪些
- 犯罪构成具有什么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