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立法有什么缺点

【合伙】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立法的不足之处
中国创业投资立法的最大特点-地方立法推动中央立法。由于创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业内人士(包括立法者)对其认识不一,导致立法更为滞后,因此初期并未出现较高层次的立法。创业投资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为推动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地方就只得先于中央统一立法进行地方立法。最终,地方立法的增多与成熟促使中央进行统一立法。
这个过程中,地方性创业投资立法势必受到整个中国法律体制的限制,实践操作困难。中国的有限合伙立法正是面临如此困境。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立法对有限合伙法律地位的确认也反映了市场经济对有限合伙的肯定。
应当承认,有限合伙制度作为市场主体立法或者民事主体立法的一部分,根据《立法法》规定,理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法律做出规定,而不应由地方性立法做出规定。地方性立法突破现行立法、确认有限合伙法律地位的做法,固然不合法治精神,侵害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但在中央立法不允许、甚至禁止有限合伙的情形下,为有限合伙谋求在一定区域内的法律生存空间,实属无奈之举。立法固然要强调了法律的确认功能,但也应注重法律的预测功能和超前性。未能充分考虑法律的适应性,对有限合伙制度的遗漏,是现行《合伙企业法》最大的缺憾。
可以讲,北京天绿创业投资中心夭折的事例正是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有限合伙立法及配套立法所致。相比之下,赛富成长基金(天津)创业投资企业应属幸运儿,但是该基金作为创业投资领域的独行者,亦步履维艰。从该基金获得商务部批准设立至取得营业执照,每一个主管部门都是第一次处理该类型企业的申请,层层审批,最终居然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依据现有相关创业投资规定,有限合伙制度只能借助于“非法人制中外合作企业”形式,换言之,内资创业投资根本无法直接取道“非法人制”实现有限合伙制度的设计。
为了鼓励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度的优势,我们需要在大胆借鉴国际惯例与经验的基础上,修改现行《合伙企业法》和配套立法,早日移植国外的有限合伙制度。唯有如此,创业投资事业方能借助于有限合伙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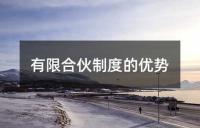
有限合伙制度的优势。有限合伙制度能够激发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实现投资者与经营专才的最佳组合,并有利于避免双层征税和降低税负。此外,有限合伙的经营活动具有更高的保密性,满足了合伙企业债权人和政府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这些优势共同推动了有限合伙的发展。
-

目前的私募基金以能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为准。私募基金组成形式主要是哪一种?大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公司制的,少部分采取有限合伙制。而私募基金募集的对象是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而私募基金则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很低,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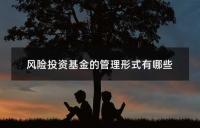
风险投资基金一般由风险投资公司管理,一家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公司往往管理数只甚至数十只风险投资基金,基金的管理形式分为信托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风险投资的运作包括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价值增值型的管理是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的重要方面。风险投资机
-

16号文在国家法规层面上,首次确立了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原则。通过上述规定可见,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实行的是“先分后税”的原则,即在基金层面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由基金的合伙人在取得分成收益时分别纳税,避免了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双重征税
- 有限合伙制度的优势有哪些
- 有限合伙制度的确立有什么好处
- 如何完善有限合伙设立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