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先定原则是什么

本来,行政处罚行为是意思先定的典型。但是,随着行政程序的法制化,特别是作为行政程序法和自然正义核心的行政听证程序[6] 的建立,使得相对人有机会参与作行政处罚的意思表示,可以与行政主体的调查人员平等地讨论证据的真实性、事实的客观性和适用法律的准确性,因而行政处罚行为已不仅仅是行政主体的意志。不过,听证程序的建立和实施,并没有改变行政处罚的先定力。这是因为,不论职能如何分离和相对人的意志怎样,主持听证的法律主体仍然是行政主体,证据是否真实、事实是否客观的最终认定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律最终适用权仍然属于行政主体。除了职能完全分离的情形外,这个行政主体就是听证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或即将与相对人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这种最终认定权和适用权不会属于相对人,也不会属于双方当事人以外的作为第三方的司法机关。因此,相对人的参与并不能阻碍行政意志的形成、否定或拒绝行政主体的意志,并没有改变行政处罚行为作为单方行为的性质,并没有使行政处罚行为成为一种双方行为。
从行政处罚的先定力和听证的关系上说,我们在行政处罚的听证中必须避免两种误解。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等行政程序制度可以使公民“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7] 我们认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与行政主体的优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如果没有行政主体的优位,也就没有行政行为的先定力。我们尽管不能武断地认为上述观点是一种否定行政行为先定力的观点,但却可以说是对听证等程序的一种误解。我们认为,相对人在程序上的参与,确实能影响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但却是有限的。在听证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相对人的意志只有在为行政主体所接受、采纳时,才能体现在行政行为中。这种接受和采纳并不是相对人强制的结果,而是出于行政主体的自愿,并且为行政主体的意志所吸收后就成了行政主体本身的意志。我们同时认为,听证的设立和实施,也能使行政主体的意志影响相对人的意志,即能够用与公众讨论的方法来说服或指导相对人自觉接受行政意志,弱化容易导致对立的强制。[8] 双方意志的相互影响,是以行政意志影响相对人意志为主要方面的。通过这种相互影响,使最终形成的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准确性、可接受性和效率性。[9] 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讨论这种相互影响时,不能运用19世纪的以对立和制约为核心的法治理论,而应当运用20世纪以来的以信任和合作为核心的法治理论。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其实就是相对崐人对行政主体全面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一种合作,也是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一种尊重,旨在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10] 因此,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意志相抗衡,并不是设置听证等程序制度的目的。另有一种观点,就是把行政行为的先定力误解为行政主体可以专横和武断。如果这种偏见得以存在和流行,那么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制度将流于形式,行政法治的成本将得不到回报。其实,听证等程序制度作为“一个非武断的政治体系”,[11] 是对19世纪只注重结果即行政行为的形式法治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是20世纪最重要的行政法治成果之一。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意思先定的前提下,充分尊重相对人的意志,更为全面、客观和合理地作成行政行为。因此,我们强调意思先定,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可以专横和武断。
总之,我们应当将听证程序置于行政处罚的总框枷内来加以认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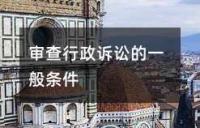
行政诉讼的审查条件及合法性审查原则。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诉讼时,需查明是否存在重复起诉、是否符合生效裁判效力所羁束的标的以及起诉状是否符合形式要求。同时,合法性审查原则包括适用主体、审查方式、审查范围和审查标准。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法院应遵循以上原则,确
-

环境侵权案件中法院如何认定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环境侵权案件的证据收集主体广泛,包括当事人、律师、行政执法机关等。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我国实行“差别待遇”的举证责任原则,原告应收集有关开发建设、排污、污染物浓度和数量等证据,被告应收集不产生、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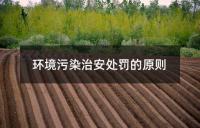
环境污染治安处罚的原则,包括处罚法定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和责任自负原则。处罚必须依法进行,主体和依据需是法定的;处罚应与违法行为情节、性质、事实及社会危害程度相一致;违法环境行政相对人应亲自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得由他人代为承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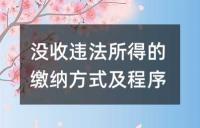
没收违法所得的定义和实施方式,包括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剥夺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财物。追缴和处理违法所得应遵循“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违法所得的计算需要准确查证,全面收集相关证据并遵循“全面调查、客观公正”的原则。缴纳方式包括当事人自愿缴纳
- 处罚法定原则
- 行政拘留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 刑事赔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