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与行政垄断规制困境——泰国两则反垄断案例的

泰国两则反垄断案例的分析
一、泰国有限电视公司捆绑销售案
泰国1999年颁布的《贸易竞争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期望通过该法律来起诉垄断企业,保护消费者利益。1999年底,泰国贸易竞争办公室接到了两个主要案件。
在第一个案件中,泰国有线电视公司IBC和UTV合并成为有线电视公司UBC。在合并之前,IBC和UTV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节目组合。然而,合并之后,UBC改变了节目组合,并提高了安装费和每月收费。UBC申请不向新用户提供最便宜的组合,并拒绝向其他用户提供便宜组合的详细信息。UBC还承诺提供一个替代的高价格组合。贸易竞争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业委员会来调查消费者的投诉。调查发现,UBC受到了高市场准入壁垒的保护,实际上成为了国家有线电视市场的垄断者。有足够的证据表明,UBC收取的服务价格过高,并限制了新消费者的选择,使他们只能选择一个高价组合。尽管UBC承诺维持服务质量,但在《贸易竞争法》颁布实施后,它实施了捆绑销售策略。
二、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问题
在中国,石油、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竞争机制的引入仍停留在分拆原有垄断企业的层面,尚未形成规范的进入和退出制度。虽然从市场份额等标准来看,这些行业可能不构成垄断,但从垄断判别标准的角度来看,行政性准入限制广泛存在,这些行业仍然是完全的垄断行业。因此,垄断行业改革陷入了僵局。
与此同时,中国的反垄断立法也出现了重大变化。2006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对《反垄断法》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其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章节被整体删除。此外,中国反垄断执法权力的配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三个部门相继介入反垄断立法工作,导致《反垄断法》的出台面临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大量的宣传和推动,另一方面却缺乏明确的牵头机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三、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与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反垄断法本身并不能自动促进竞争,其关键在于执法权力的配置。在国有经济比重高、行政垄断广泛存在的经济体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行政垄断需要区别对待,有些行政垄断是反垄断法需要约束的对象,有些则应归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如果不能将二者分开,将会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
通过对泰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的两个捆绑销售案例的分析,可以考察泰国的行政垄断、利益部门博弈与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问题,并通过这个角度反思中国的行政垄断规制策略和反垄断执法权力的配置模式选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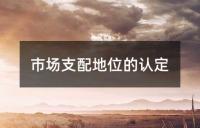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问题,包括在法律中市场份额对经营者市场地位的重要性,以及相关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的规定。市场份额的推定依据具体情形而定,同时允许经营者通过事实进行反证。如果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能证明自身不具有支配地位,则不应认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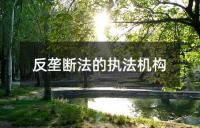
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职责划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国家工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不享有反垄断行政执法权,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根据需要授权相应机构进行反垄断执法工作。此外,
-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同法律属性、目的、内容、手段以及国家在调整相关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反垄断法属于公法范畴,旨在创造合法竞争的市场环境,主要调整市场构成,防止经济集中和滥用优势。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私法范畴,旨在规范市场秩序和保
-

垄断行为的分类,包括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同时介绍了垄断协议的横向和纵向分类,以及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和豁免情形。其中豁免情形需要满足法定正当性要求,并证明不会对市场竞争
- 垄断行为的认定规则及程序
- 自然垄断的定义和原因
- 建立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